在上海,木心同朋友之间交往最频、饮酒聚餐最多、恩恩怨怨或推心置腹甚而深夜密谈或手书墨笔互赠诗词最多。但也是在上海,木心度过了人生最艰难也最隐忍的一段时光。
编者按:
作家、画家木心的艺术生涯,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上海时期,从他20岁离开家乡乌镇来到上海,直到1982年远去纽约,长达35年;二是纽约时期,从1983年至2006年回到故乡,历时24年。
木心的纽约时期,完成和发表了大量的文字作品、绘画作品,尤其在陈丹青以及国内外众多木心研究者的热心推广下,崇敬木心的读者们得以一窥木心当时的生活与生命。占据木心生命更长阶段的上海时期,却因为木心本人的缄默而始终不为世人所知。
机缘巧合,当时尚年幼的铁戈得以结识上海时期的木心,难得地成为木心的忘年之交,并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木心还是“孙牧心”时的上海生活。“正是在上海,木心同朋友之间交往最频、饮酒聚餐最多、恩恩怨怨或推心置腹甚而深夜密谈或手书墨笔互赠诗词最多。”
但也是在上海,木心度过了人生最艰难也最隐忍的一段时光。直到被平反前,木心都在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做着最脏最累的差事,还坚持把自己收拾得齐齐整整,不让身边好友看穿。只是偶然一次,他向救命恩人胡铁生之子胡晓申透露自己当时的心境:“我白天被人斗,被人打,干最脏最苦的活,都没有关系,晚上回到家里,是我的世界,我就是王子,我可以写我喜欢的,画我喜欢的。”
木心把隐痛藏在心中,从未向上海的好友提起。在2006年从纽约返回故乡经停上海时,木心也没有拜访任何一位上海时期的好友。而好友们过去就明白木心的怀揣心事、深藏不露,此时也尊重木心的有意回避。
时过境迁,木心和他几位上海时期的老友都已故去。当时一群人中最为年幼的铁戈,也已过古稀之年。几番犹豫之后,他终于提笔写下《木心上海往事》一书,以期梳理木心上海时期的生活状态,从记忆中探索他精神世界的轨迹。
下文节选自《木心上海往事》一书,文章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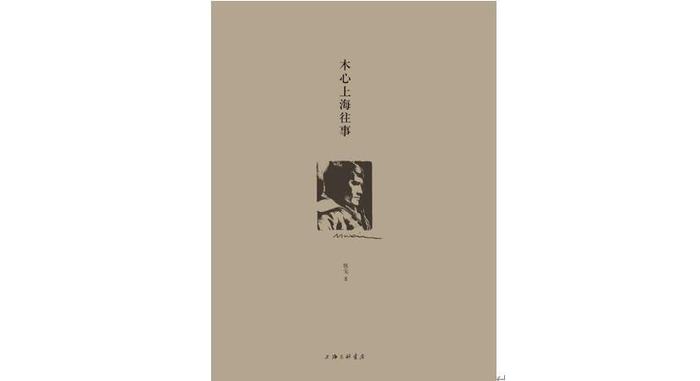
撰文丨铁戈
摘编 | 肖舒妍
01
如果只能用一个字来表达从前的木心,这个字也许是“难”。在《从前慢》这曲慢悠悠的旋律背后,有一位无声的《从前难》的木心。“声声慢”,怎一个愁字了得,从前的木心,怎一个“难”字了得。
在木心漫长的上海时期中,直到他在被平反之前,有一段最为严峻的时刻,如今无论怎样回忆木心,缺失了这段时间的记叙,将是一位不完整的断层了的木心,这也是木心最为沉默的时期,对再好的朋友,他也从来只字不提。
木心在《云雀叫了一整天》中说:“倪瓒的‘一出声便俗’,他用了一时,我用了一世。”木心佩服倪云林辈羞辱后“不出声”,这是他一生的境界和写照,从不诉苦、抱怨、伤感。
从 1972 年 2 月到 6 月,木心曾被关禁在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的防空洞里,隔离审查。审查暂告段落之后,开始了漫长的监督劳动。那段时期,白天他必须一早到厂里报到,然后开始一天的监督劳动。到了傍晚下班,才拖着劳累的受尽侮辱的身心,疲乏地回到住所,在属于自己的时空里写作或作画。只要可能,他也会同个别的朋友见面,吃饭饮酒,放松自己,获得极大的慰藉。
即使我见到木心,或去他住处拜访,这段时期所备受的折磨,他也从不吐露所受的遭遇。当时朋友们只知道他在创新工艺品厂上班,当问起他干什么工作时,他总是轻松地回答说干些杂活,其他一字不提。如今他在那段时期里受到的凌辱虐待,略有披露,当时朋友们都一无所知,具体的情景,偶然之间只有一位朋友亲自见到,那是绝对真实的见证。朋友名为梅文涛,如今还在,也是朋友圈里出色的画家,同木心也很熟悉,性情温文儒雅,他在虹口区溧阳路的家,也曾是朋友们经常聚会聊天小天地。

梅文涛当时也在设计公司工作,与木心所处的创新工艺品厂属同一个公司,一次他到木心的厂里去联系设计业务的工作,刚进厂门,一眼看到木心穿着打了补丁的工作服,弯身低头,用双手在厕所通到墙外的阴沟里捞污秽堵塞的垃圾,其景不堪入目。这时的梅文涛惊讶不已,完全出乎意料,难以相信这就是平时见到的、衣冠整洁令人起敬的木心。正巧木心无意间抬起头,一瞬间看到了梅文涛,尴尬不已,立即低下头,避开碰撞的视线。其心情复杂悲哀,可想而知。见此情景,惊讶之中的梅文涛也不敢上去同木心打招呼。两位平时熟悉的朋友如同陌人,擦肩而过。这一瞥将木心当时的处境展现无遗。
平时木心总是微笑地说在厂里“打打杂”或“杂务工”,原来是每天都在打扫男女厕所,干最脏的活。事后梅文涛也没告诉任何朋友,替木心“保密”,木心也从不提起见到梅文涛的事。
2016 年春节期间老朋友聚餐,在座恰好大都为木心当年的朋友,我同陈巨源、唐焘兄妹、林正平夫妇都在,席间不知不觉又提起了木心。时过境迁,梅文涛终于忍不住向大家吐露了此事。听梅文涛这么一说,当时的我不禁感同身受,朋友们也都为此叹息。
如今大家几乎都知道,木心在获得平反之前,有过一段漫长的苦难经历,尤其是从 1972 年到 1979 年在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这段时期,但具体细节很少有人知道。
当年的这个厂,是那个时代小小的历史缩影。该厂位于市区中心地带的石门二路 266 弄,简陋的厂房处在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居民弄堂里,由旧时名为“同善堂”的尼姑庵改建。大约 1964 至 1965 年间,经历了一番历史的变迁,同善堂关闭了,不久成了一家安置残疾人的福利工厂,原庵里的尼姑大多进厂做了工人。刚开始的时候,厂名为“工艺美术模型厂”,1966年之后,厂名顺应红色潮流,改为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这家不足百把人的小厂非常奇怪,听弄堂里居民所说,这家厂有三“多”,一是曾经的尼姑和尚多,二是各种残疾人多,三是有问题的人多。所谓有问题的人,就是各种运动的对象,所谓“牛鬼蛇神”。据当时弄堂里的居民说,虽然那些和尚尼姑还俗了,但其装束还是和常人有点不一样。残疾人一看便知,不是哑子跷脚,就是智力不全精神残疾。而那些可能有问题的人,常常是居民中阿姨妈妈们指指点点的对象。不久,厂里多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最让人觉得好奇的,是他不同寻常的穿着打扮。在那个年份里,所有的人都衣着相近,极其简朴,而这位高个子中年男子却与众不同,不仅眉清目秀,每天穿过弄堂上下班时,人们总是见到他身穿笔挺的风衣,头戴一顶深藏青色的法兰绒帽,就这一身穿着,在当时是十分引人注目。
弄堂居民们很快有人打听到,这人名叫孙璞,还没结婚。于是有热心大妈想帮他介绍女朋友。那时厂里还俗的尼姑有好几个嫁给了同厂职工,连法慧师太都嫁人了,厂里的厨师,娶了弄堂里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一些残疾青年也一对一对地谈起恋爱。可是孙璞从来不理人,热心的居民大妈们连一句话都同他搭不上,于是立即就有了另一种风言风语 :“这家伙像煞有介事,扮得像个艺术家,其实是个有问题的人。” 于是就没人敢凑近他了。
有位曾经居住在这条弄堂里的居民岳群,在《世纪》 2016年第 5 期撰文回忆道 :“有天听到模型厂里人声鼎沸,口号阵阵。我便随大家跑过去看热闹。只见那个孙璞(当时人们不知道他的笔名木心),被人反扭着双臂,强制跪在车间的水泥地上。听到前面几个凶巴巴的戴着红袖章的人七嘴八舌的训斥,看热闹的我总算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弄堂里厂门边的墙壁上,画着一幅孙璞绘制的体温表广告画,在大大的体温表画面上写着一行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天天看到这张广告牌,从未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那个造反派却说,将语录写在表上是别有用心。只见孙璞涨红着脸,认真地辩解。双方争得特认真,却十分滑稽,引得围观者哄堂大笑。这时恼羞成怒的造反派冲过去,对着孙璞一顿乱打,有人喊起了‘打倒孙璞’的口号。但无论造反派怎样羞辱和折磨他,孙璞始终都没有承认。弄堂里的人私下议论说,这个人看着斯文,倒还是蛮吃硬的。”
“后来孙璞被关进了公安局,听说是什么‘现行反革命’的罪名,不知同我所见到的那幕闹剧有没有关系。再后来,看到他回到了厂里。最大的变化是,他不再穿挺括的衣服,成天穿着旧工作服,提着拖把、扫帚,或打扫卫生,或干粗重杂活。那时的他更是低头不看人,以沉默面对世界。”
02
木心即使在平反之后,也从不向朋友们提起往事,只是告诉大家,是新上任的手工业局的局长胡铁生帮了他,让他获得平反,从创新一厂里捞了出来,他对胡铁生充满了感激。就这么寥寥数语,没有任何细节。也从不提起怎么会一下子就任令人羡慕的工艺美术协会的秘书长。对于木心来说,这种人生的大起大落,一概宠辱不惊,不值得一提。
尽管木心坚守倪瓒的“一出声便俗”,从不向他人具体地诉说自己所受的屈辱和折磨,以及其中的细节,但仍有昔日同事、朋友、亲眼所见者的回忆。有位当年创新工艺品一厂的职工,有更为详尽的回忆,曾经发表过《木心闭口不谈的隐痛岁月》,文章署名秦维宪。从细节上看,基本上同胡晓申、我的朋友梅文涛,以及其他目睹者的回忆符合,比较详尽,值得摘要引用。作者秦维宪认为 :“木心对这段岁月守口如瓶,在所有文字记载中唯独‘遗失’了这段炼狱般的‘断层史’。这也许反映了这位奇才‘孤傲、独特、飘逸’的个性,还是他不愿揭开自己的伤疤呢?如果缺少这段路途,他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现我以切身经历、真实的笔触尝试着还原他那段‘遗失’的隐痛岁月。 ”

秦维宪是 1972 年 12 月下旬从培明中学毕业分进了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这家小厂,在石门二路 266 弄 13 号,曾经是破尼姑庵,是做塑料花的车间,几无劳动保护,注塑的毒气无孔不入地侵袭着工人的肌体。他回忆道 :
“一次卸完货,从拉料车间的破门帘后闪出一位年近半百、风度儒雅、着补丁整齐的劳动服之人,他双目如炬,深藏的眸子冲我一笑。我自幼喜读古书,讶异于此人颇有仙风道骨,遂脱口一声 :‘师傅,您好!’不料,他脸色骤变,连连摆手,示意我不能这样称呼。以后,我们多次相遇,他总是一迭声说咱俩有缘。我从老师傅口中得知,此人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高才生,其知识之渊博,在上海手工业局无人能望其项背,但也是每天要请罪之人。任何人都可以侮辱、欺凌他 ;而他却整天佯装笑脸,对任何人都得点头哈腰;特别是每逢元旦、春节、五一等节庆时,更被训得狗血喷头。”
“且不说他经常挨打受骂、被批斗,单以强劳力而言,他干的是厂里最苦最累最脏的活,除了倒便桶(厂里没有正规厕所)、通阴沟、铲车间地上的机油外,还经常跟着铁塔似的装卸工扛原料 ;其中通阴沟、铲机油最累,我曾帮他通过阴沟,阴沟内彩色的胶水般的污泥,足以将得过肺病、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木心击倒!”
“而木心一生中干得几近垮掉的重活,是 1975 至 1976 年的翻建厂房,他每天要推无数次的垃圾车,又经常加班加点,生病了也不敢上医务室,悄悄地去药房买点药。有一天黄昏,正发高烧的木心,涨红着脸、喘着粗气,从工厂后门推车挪向山海关路,可怜他双腿打颤,扶着墙慢慢倒在地上 ;少顷,他又咬紧牙关爬起来……”
“木心为了排遣痛苦,便大量抽烟,似乎烟雾会带他遨游在无限美妙的艺术世界里。令人心酸的是,木心拿的是生活费,为了省一角四分车钱,他一年四季风雨无阻,都是走十几公里上下班,因为抽了大量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以致给肺部留下严重的隐患。”
“记忆中,无论木心经受多少打击、劳作多么辛苦,下班后一定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冬天,他戴一顶黑色的鸭舌帽,系好围巾,披一件整洁的旧黑大衣,从容走向晚霞燃烧的前方 ;他还在极其有限的生活费中省出小钱,慰劳自己,如他喜欢吃‘凯歌’五分钱一只的葡萄干面包、西海电影院对面小吃摊上一角钱一客的生煎包子,在夏季买一根八分钱的雪糕,立马像顽童般兴高采烈。这时,木心凸显了他单纯、幼稚、可爱的一面。”

03
紧接着作者写道 :
“1982 年,木心飞赴美利坚,瞬间从工友们的眼中消失了,当 2006 年他在乌镇旅游公司总裁陈向宏的安排下落叶归根后,乌镇便像磁铁般吸引了不少工友,他们多想见见这位可敬可爱的睿智老人啊!”
然而,木心拒绝见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的任何人!
我深深理解作者的心情,他们怀着一颗迫切的心想再见木心,并非以为当年对木心的“滴水之恩”,今日应有回报。但木心拒见当年工艺品一厂的任何人,确实令他们一时难以理解。
“2007 年仲秋,我们小兄弟聚会,小华兄叙述了木心拒见工友的经过。第一个去见木心的是巧生师傅,这是一个古道热肠的直筒子,他作为我母亲的学生,从启蒙教育中灌输的恻隐之心,依然沉淀在血管里。已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家回忆道:木心家里成分是地主,自己又成了‘黑五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肯定被厂方抓了阶级敌人的典型,但他的美术设计水平很高,不要说厂里了,就是全上海都无人可及!我对木心总的看法,此人心气很高,有技术、有才华,过去的种种遭遇没能让他放弃所掌握的知识,是金子总会闪光的!有了这层看法,所以当木心回国后,我立即坐火车去看他,遗憾的是,他客气地让秘书回拒了。”
“木心怕见工友,是为了不再揭开业已流逝的伤疤,将那段痛苦的岁月,永远封存在心底。人们只要看一下木心故居他自撰的生平就明白了,他自踏上社会的工作单位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唯有 1967 至 1979 年在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的那段经历是空白,即用了‘我厂’作为替代。 试想,如果木心见到了昔日的工友,即使如我这样算他的学生,他立即会产生蝴蝶效应,联想到昔日的苦难,乃至浮现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与事。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去打扰木心呢,让他在归隐田园的桃花源里安度晚年,不是很好吗?由此,我真诚地希望工友们理解一个曾经差点被整死的老人,恐惧迟暮之年噩梦缠身的悲苦心境!”
木心拒见当年苦难时期友善对待他的工友们,作者分析道 :“不难推论,木心时刻在想念昔日关照过他的工友,只因创新厂对他的伤害实在太深了!”
的确,这是木心拒见当年工友们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毕竟不知其所以然。更没明白,在实际上,木心并不是他们的“工友”。戴着“帽子”的木心同他们之间,实际上属于社会上的“异类”,同所有其他的群众处在一个完全不平等的地位。这种特殊的关系是时代因素所形成的,同“友”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情谊确实十分珍贵,但毕竟没有大到足以弥补木心的伤痛,且是任何人难以弥补的。他们很难理解 :在那段时期,戴着帽子、被迫接受监督、强迫劳动,那种他人即地狱式的最深刻的感受,远比监狱更为折磨人。
如果单独关禁,你只与自己相处,一切自己承受,面对的只是自己。如果关在大牢里,周围的人也都是囚犯,所以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无论怎样,你是同人在一起。但在社会上,孤身一人处于群众的包围之中,任何人都有权侮辱你,欺凌你,打骂你,不需任何理由,仅仅因为你是异类。稍有反抗,定会招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此外,你还得干他人所不齿、最苦最累最脏、人格最受羞辱的活,包括众目睽睽之下,每天都得去打扫男女厕所。这时候的你,既如一个人处在鬼蜮之中,又如一个“鬼”处在人群中,同时遭受着这双重的酷刑与荒谬。这种强烈的对比,会最大限度地碾压一个人的自尊,精神的摧残所造成的心灵伤痕,比肉体上的创伤更为严重,既难恢复,也永难抹去。
我理解木心为何在乌镇幽居期间,拒见当年那个工厂的任何人。但那些工友也绝没想到,那时真正给予木心精神支撑和安慰的,是他下班之后,偶尔能与自己的朋友们饮酒会面,这是那些善良纯朴的工友们所无法知悉的,也是木心无论如何不会向他们透露的。对于木心来说,那是相互隔绝的阴阳两世界。
本文节选自《木心上海往事》,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方授权刊发。
撰文 铁戈
摘编 肖舒妍
编辑 徐伟
微博编辑 王易凡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