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伟大已无需赘言。在他最后一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一个平凡的老人,也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试图抓住每一瞬间去努力生活、感受、工作,思考着幸福、道德、存在与上帝。从这些日记中,我们或许可以知道托尔斯泰之所以是托尔斯泰的部分原因。
作者|托尔斯泰
译者|任钧
摘编|张进
一月十四日
早晨起床。散步。有了好的感想,且把它写下来吧。
(一)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神的成长。老是想着结果,对完成天职,是有害处的。甚至对那些由我们所创造的某种看不见的工作,或是对我们所能看得见的结果,都是有害处的。“拿着犁回头向后面看的人,是没有希望入天国的。”
我们在人生当中的境遇,很像马,或是一般的拉着车子的动物。对于那动物,动作,向前进,乃是本来的职责。
同样地,对于人类,本来的职责,就在于精神的完成当中。动物拉着车子。并且不管你愿不愿意,当动物一动作,那给动物所拉着的东西,也就不知不觉地动作起来。同样地,在人类道德的成长上,也是一个跟着一个地行动起来的。(人类时常看得见:他自己的行动怎样地帮助了别人的行动。)
因此,彗星并不可怕。完成于精神界的一切东西,是不会由于物体的破坏而被破坏的。
(二)现在的生之意义,时时刻刻越发明了地显示出来了。生活,即我们的努力,只有现在才会有。而且现在乃是精神的存在,因此精神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存在。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想象,不过是存在于现在的向导工具罢了。(这还不好。但在想的时候觉得这是好的一种。)
现在,快到十一点了。坐在桌子跟前着手写信和做事情。做什么事呢,我还不明白。稍微修改了一点儿《教化的泉源》。跟朵香一同骑马散心。夜晚跟布里金一同度过。跟塞略且谈话。他同意我的见解——人们的内心都居住着上帝。不健康。胃痛。

一月十五日
健康好像渐次地坏了下去。在来信中,引得起兴趣的很少。继续从事《教化的泉源》的工作。弄好了五六天的。没有骑马到什么地方去。只是稍微走了一些路。须得写下来的是——我清清楚楚地想起来了:现在已是八十二岁的我,意识到自己,正跟五六岁时意识到的自己完全相同。意识是不动的。因此,存在的,只是那被我们称之为时间的东西在运动。如果时间是个进行着的东西,那就不能不应有停止着的东西。我的“我”这一意识,就是不动的。关于物体和空间,同样地也可以这样说。要是有什么存在于空间里面的话,那我以为当然也就该有无形的、不占据空间的存在。但我还不明了可以把后者说明到怎样的程度。
吃饭去。夜里没有什么特别可记的事情。
三月二十一日(二十日、二十一日)
昨天身体非常不好。伤风。咳嗽。发热。完全不想吃东西。我想,这也许是死的通知。但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苦痛。这么一想,心情却变好了。没有到外边去。写信,修改笔记。夜里健康情况更加不好。
今天也是一样。早晨很痛苦,但一会儿就渐渐地好起来了。又做事情。接着读有兴趣的信。然后读爱尔纳费尔特(译注:一位芬兰作家)的著作。我对他的戏剧不很有兴趣。
现在是十点钟。仿佛好了很多了。沙夏又病了,但并不严重。我的心情非常好。能够清清楚楚地想事情,这是很难得的。我想把所想到的写下来,但不写也好。
达尼亚很可爱,我十分喜欢她。
「三月二十二日。要是还活着,就得写。」(译注:托翁晚年的心情是,抓紧现在的每一刹那,不断地努力工作,但同时也不断地感到死亡的临近。结果,就常常在写完今天的日记后,预先写下明天的月日,并附注“要是还活着的话”这些字眼。)
四月十七日
我总以为不能再坏了。但今天的心情比平常还要糟。艰苦奋斗下去吧。柴尔特科夫寄来了一封很好的信。还收到了中国进步集团的杂志。(译注:这一天,托翁收到了一本中国进步青年所主办的杂志,名叫《寰球中国学报》,托翁读了其中好几篇论文。其中,《论中国文明》一篇,尤引起他的注意。该文中有“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一语,特别使托翁感到兴趣。据说,他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倘使我年轻些,我定要到中国去。”)很有趣味。什么地方都没有去。饭后,校订分册。全部都得更改。
另外没有什么可以写的。
「三月二十二日。要是还活着,就得写。」

四月二十日
依旧还活着。起来得不很早。在嫩枞树下散步。蚂蚁在忙碌地劳动着。写了一点儿什么东西。那位对我显然没有好感的上校又来了。校正分册四种:《罪》《恶的诱惑》《迷信》和《虚荣》。不坏。和布尔卡科夫一同骑马散心。引得起兴趣的来信并不多。夜里,读甘地的《文明论》。非常好。
要写下来的是——
(一)真正进步的活动,是要经过好几世纪的。为要前进一步,整个世纪的死亡是必要的。如今,那些不以自己的财富为可耻的富裕的贵族阶级,那并非由于实际生活和意识之不一致所生的苦恼,而只是生活在作为职业的革命虚荣里面的革命家们,都不能不灭亡了。因此,第二个世纪,即对孩子们的教育,变成了怎样的重要啊。
(二)日本人把基督教当作文明的附属物之一而接受着。他们果真能够像现代欧洲人一般地,使基督教变成没有害处,且不会破坏他们从文明当中所获得的东西吗?
(三)大多数人都只是过着动物的生活。并且对于人世间的各种问题,只是盲从着社会的舆论。
(四)思想上的努力,正如可以长出大树的种子一般,在眼睛里是看不见的。但人类社会生活的明显变化正发生于其中。
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补记)
五月二十六日漏记了,今天是二十七日。
昨天起来得很早。记得自己对那些有所请求而来的人好像表现出不好的态度。鼓起劲把分册搞了相当长久的时间。五篇已经完全弄好了,还要再写两篇。跟朵香骑马做短时间的散心。沙夏要回来了吧。
夜里,阅读维白尔(译注:莫斯科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谈罗马的论文,写得很好。想要写一篇以杀了人的兵士做题材的东西。
早上,不,错了,应该说昨天夜里,醒得很迟,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新的极强烈的感想——
(一)我开始鲜明地感到了这世界一切所谓偶然性的东西。我——这么明了、单纯、聪明、善良的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混乱、复杂、狂妄、罪恶的世界里面呢?为什么呢?
(二)(关于裁判)啊啊,这些不幸、愚蠢、粗野、自满的恶汉!倘使他们身穿官服,坐在那覆着绿绒的桌子跟前,把记载在那以侮辱人类为能事的可厌的书本当中的毫无意思的语句,装腔作势地穿凿附会,翻来覆去,并因此而理解他们自己究竟干着怎样的勾当,那该多好呵。倘使他们能够理解那被他们自己名之为法律的东西,对于那写在全人类心灵上的永恒法则只是一种粗野的嘲笑,那该多好呵。
有些人并没有什么恶意,在被称作教会的场所用枪打死了鸟儿,就被认为冒渎神圣,而被处以徒刑。但反之,在这世界上,对于最神圣的东西——人类的生命——不断地实行冒渎神圣,并以此为常而生活着的家伙们,却洒脱地不会受到任何处罚。
皇帝自己就教导着无罪的儿子去杀人。而且这正是信奉基督教的人们干出来的。一个兵士,自以为没有必要,不想服从,就开小差。啊啊,描写这件事情是多么必要呵!我又怎样地想要写呵!
七月七日
还活着。但实在是个很坏的日子。因为依旧没有精神,什么事也没有做。连校对工作也没有做。骑马到柴尔特科夫那边去。一回来,索尼亚就大发脾气,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平静下来。夜里读书。深夜,戈尔登维则尔和柴尔特科夫来了。索尼亚虽是听到了他的说明,但还是没有平息。当夜晚来得更加深沉的时候,我跟索尼亚好好地谈过话。几乎整夜没有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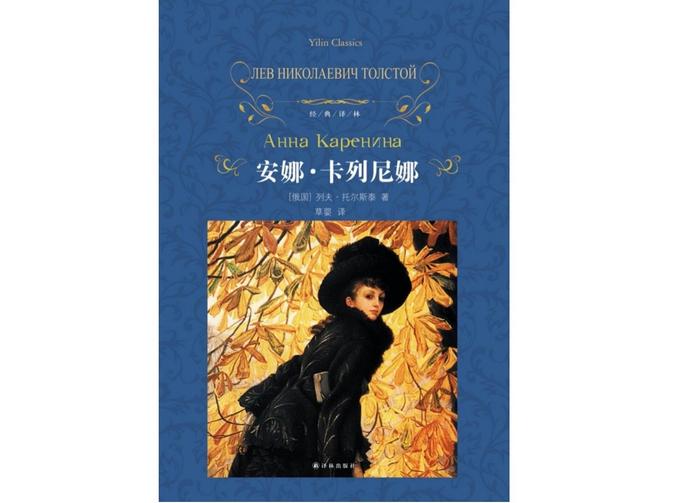
七月二十七日
一切如常。但这也只是像暴风雨前的静寂。安特列来了,讨厌地问我是否写过什么东西(译注:托翁的儿女们特来向他问及预立遗嘱的事情)。我说,我不想回答。非常痛苦。我不相信他们只是期望着金钱。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对于我,一切唯有善。睡吧。塞略且来。达尼亚来信,说是要来。米夫·塞尔该也来了同样的信。且看明天的情况吧。
(一)刑罚的历史,就是刑罚的不断地废止。——叶林(译注:德国的法学理论家)
(二)我们能够从偶然的、明显地被认为是盗贼的盗贼手中逃出来,但我们却委身于连续不断的、组织化了的、被认作恩人的盗贼之手,即政府之手。
(三)人把自己认作神,是对的,因为上帝存在于他内心。把自己认作猪也是对的,因为猪存在于他内心。但当他把自己的猪认作上帝的时候,他却犯着可怕的错误……
(四)向着自己这样地询问,是很好的:你是否已经不谈个人的幸福,已经将上帝的工作认作自己的使命,而不管人们的责难和轻蔑?向着自己这样地询问,然后再做如下的回答,那就更好:是的,可是,做着上帝的工作而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感,这种情形是绝对没有,也决不会有的,幸福就在这里。
七月三十日
身体稍微好了点儿。睡得好。来了好几封非常有兴趣的信。除开写信,没有做旁的什么事情。骑马到帕沙朵夫的地方去,送给他校样。在家里吃饭。颇夏领孩子们来。戈尔登维则尔也来过。跟儿子们依旧很觉疏远。痛切地感到沉默是必要的。努力吧。送左夏出去后就睡觉。
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说是因为大家没有请她玩牌,很是懊恼。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沉默是必要的。
八月三日
还活着。可是很忧郁。校对的工作倒搞得很好。引用了帕斯卡尔值得惊叹的文句。阅读帕斯卡尔所写的东西,意识到这位死了好几百年的人竟跟自己完全一致,感动之余,不禁泪下。既然生活在这种奇迹当中,此外还须什么奇迹呢?
和戈尔登维则尔一同骑马到科尔奔去。夜里又发生了一场苦痛的骚动,我兴奋得很厉害。什么工作也没有做,感到心头猛充着血液,不但不愉快,简直很苦痛。
八月十日
非常衰弱。起来得很早,但连走路也困难。总算好好地写了东西。还写了几封信。跟朵香骑马外出,很愉快。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跌倒了。她整晚没有睡,但很安静。晚间士兵们来了——三个犹太人和一个政治性的小俄罗斯人。(译注:这一天,在托翁庄园的大门对面,有两大队炮兵在宿营。官长生怕士兵跟托翁来往,就告诉他们:“他是你们的敌人!”且于日落后概行禁止士兵外出,违者就得被关三个月的禁闭。可是,没有用,还是有三个犹太籍兵士去拜访托翁,跟他谈话。当他们走后,一个军官就偕着一个文官来到了。此处所谓“政治性的小俄罗斯人”大概就是指此人。)觉得很无聊,不,宁可说是不愉快。
(一)要原谅因悔悟而变得谦虚的人,是多么容易呵。对那侮辱自己的、自信自满的人,要平抑自己心中的Rancune(怨恨)和恶意,该多么困难呵。但学习原谅这样的人们,正是很重要的事情。
(昨夜,当我给兵士写信的时候,才开始感到这可怕的事件的一切罪过。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二)所谓爱,就是在一切现象当中去认识自己。自己和全体相一致——这就是对上帝和邻人的爱。
(三)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个谦虚的人的时候,你马上就已经不是个谦虚的人了。

九月一日
今天是九月一日。昨天没有写日记。早上(昨日)跟平常般地散步,思索着一些尚未决定的事情,而且写了下来。接到几封不很有兴趣的信,然后骑马到马特维爱娃家里去。一边是值得尊敬的、强有力而聪明的、勤劳的人们,另一边是怠惰的、邪恶的、最低劣的、几乎是在动物水平上的、具有权力的人们。这一对照,给我以非常强烈的印象。我为之感到疲乏。这些游手好闲的人,完全跟疯狂为邻。吃饭。疲劳。玩牌。
要写下的感想很多,如今只写出一点儿来吧——
被赋予理性和自己内心的神性之自觉的人们,不想去发展其神性,而想要比马和鹿还跑得快,跟鸟儿一般地飞翔,消灭为他们的幸福而被赋予的这种内心的要素,而徒然努力去发展既不会被赋予也没有必要的要素。这实在是一种可惊的现象。
今天一早就起床,好好地散步。写下了为着孩子们的祈祷的词句。修改写给安希娜(译注:一位杂志社编辑)的信。现在我坐在桌子跟前,大概可以做事情吧。
稍微做了点儿事情。饭后写信给索尼亚和比留科夫。马芒托夫夫妇(译注:妻子是一个农民小学校的教师。她跟托翁通信,讨论用托翁著作做教材去教育儿童的事情)来。阔佬们的疯狂状态更是一目了然。但我跟他们玩牌,一直玩到十一点钟。真可耻。打算要戒绝一切的赌博。疲倦,就寝。
九月三日
今天早上,出去散步,走到了很远的地方,但没有到达欧布拉左夫卡村。回到家里,就以最近所没有经验过的沉醉的心情开始写作。骑马到特列哈尼特沃村的农民家里去。马跌倒了。看见一个比我的年纪还要大的老头子在打谷子,给了我强烈的印象。马芒托夫来。沙夏也来了。家里依旧充满着一股好像要使人窒息的难堪的闷气。
忍耐吧,列夫·托尔斯泰!努力吧。
夜里,不想玩牌,然而我还是围在桌边看旁人玩。
九月六日
大概是由于衰老而来的虚脱吧,早上起来时完全像病人。这很可喜:死亡的接近不但并未唤起不愉快的情感,而且还酝酿出一种高兴的心情。此外就是没有力气,缺乏食欲。从特兰斯伏尔寄来了关于无抵抗主义者们的集团的愉快报道。什么也没有吃。天已经黑了。放电影的来了。跟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谈话。一切都好。
要写下来的是——
意识、意识的本质,是难于研究、难于攻克的某种东西,即我们称作灵、称作魂的东西。意识被包含在物体的某一部分。这物体就是我们的肉体。而且这意识依据对于旁的肉体(物体)的外部关系(机关)的帮助去认识周围的世界(外界)。这是人生的本质。
十月六日
晨起,精神稍微恢复了点儿,没有那么衰弱了。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二三感想,都由沙夏加以誊清。
如今要写下来的是——
(一)在散步途中,我特别清楚而生动地感觉到牛、羊、土拨鼠和树木的生活——那些树木都各自伸张着根,做着自己的事情。它们在夏季长出嫩枝。种子变成枞树的嫩苗,橡实变成小橡树,经历着岁月,渐次生长,要保持几百岁的年龄。而且还从它们那边陆续发生出新的后继者。牛、羊、人类,也是同样的。而且,这事情进行在无限的时间里面,今后也将要同样地在无限的时间当中继续发生。不论在非洲,在印度,在澳洲——是的,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里,通通都是这个样子。而且,不止这个地球,就在跟这地球相等的数千百万的天体上边,也是同样的吧。因此,当我们了然地领悟到这一事实的时候,而要谈到任何人种乃至任何个人的伟大之类,就会变成一种使人难堪的滑稽。在我们所知道的各种存在当中,人类诚然要比其他的存在来得高超。可是,正如在比人类来得低劣的东西当中,有着我们只知道其中一部分的无限低劣的存在一般的,那比我们高超的东西,也应该有着无限高超的存在,只是由于我们不能够知道,所以不知道罢了。人类既然在这种立场上,要说起我们的伟大或是什么,实在是滑稽的。我们所能期望于作为人类自身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别要做愚蠢的勾当罢了。是的,此外没有其他……
(二)上帝在我们中间呼吸,上帝就是幸福。我们探求幸福。即不管你想不想,都在探求着上帝。我们向自己(给肉体的衣服所包藏的个人)探求幸福,不能够发现它。但,当作范例,由于我们的行为的结果(斗争、技术的完成、学问上宗教上的迷误等),就不知不觉地给他人服务着。可是,倘使我们把自己认作神,而探求万众的幸福的话,那我们也就可以发现自己的幸福。探求上帝,就可以发现幸福;要是探求真正的幸福,就可以发现上帝。是的,爱就是幸福的结果。应该占首位的,不是爱,而是幸福。与其说上帝是爱,还不如说上帝是幸福更加正确吧。
(三)人类把自己的生命意识为过去现在时常存在着的某种东西。因为“时常”这一词乃是指时间而言,所以连这词也不恰当,而要完全意识为一种永恒无限存在的唯一绝对的存在。我的肉体是从母胎内生出来的,我却是完全另外的绝对存在。
(四)对于表明了自己的信念的人们,最普通的责难就是说他们过着跟自己信念并不一致的生活,因此他们的信念并不真实。可是,要是我们认真地想来,就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理解。当一个聪明人发表着跟自己的生活不一致的观念的时候,他会恬然不去注意到那不一致吗?虽然如此,倘使他还是发表着跟生活不一致的信念,那只是表示着:他是个非常真挚的人,他不能不表明自己的弱点,而且,也不会干出大部分人所干的事情,即不会因为自己有弱点就不表明信念。
十月二十四日(节选)
今天收到两封信(译注:一封是由一个彼得堡的大学生寄来的。在信里,他责难托翁言行不一致,并从梅列秋科夫斯基所写的论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生活和创作》当中引用各种例证。另一封是由布鲁塞尔的一个德国人寄来的,因为只是谩骂,托翁并未回复)。一封是关于梅列秋科夫斯基责难我的论文的;另一封是由海外的德国人寄来,也是责难我的。真是痛苦。我疑惑地想——为什么要说别人的坏话呢?为什么一定要责难别人的善良意志呢?我开始懂得了。我们虽然不同意这种事情,然而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而且甚至于是一件好事情。倘若没有它,人类将要多么骄傲自满呵。那种谄媚世俗之见的心情,将要在不知不觉之间去代替那完成自己的灵魂的工作。别人这种不应该的憎恶和侮辱,马上就要把我们从俗见的烦虑当中解放出来,而使之转向于唯一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人生基础,即完成自己良心之意志的工作。自己良心之意志,正是上帝的意志。
十月二十八日
十二时半就寝。一直睡到三点钟。我忽然醒过来了。这时候,正跟前天晚上和大前天晚上一般地,我又听到了开门的声音和脚步声。
到现在为止的好几天夜晚,我都没有从门里去张望,今天我倒望了一下。从缝隙间望过去,只见我的书房里面灯光明亮,还可以听见衣裙的窸窣声。原来索非亚·安得列维娜正在找寻什么,大概正在阅读什么。前天晚上,她曾关照过我不要闩门。不,与其说关照过还不如说是要求过。那间屋子两边的门都是开着的,因此无论我的怎样微末的动作她都清楚。这样,不分昼夜,我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她都心头雪亮,都不能不在她的监视之下。
又听见脚步声,悄悄地小心谨慎地把门打开,她就跑过去了。为什么这事情竟在我的胸中激起了这种难忍的憎恶和愤慨?——我不知道。我想要睡眠,却睡不着。翻来覆去地过了一个钟头左右,就点燃蜡烛坐了起来。
开开门,她跑进来了,问我:“你的身体好吗?”说是因为看见我的屋子里亮着光,很觉惊奇。这加强了我的憎恶和愤慨。我气喘吁吁的,数数脉搏是九十七次。已经不能够躺下来,我突然下了离家的最后决心。写信给她,并开始准备必要的东西。然后就只剩下走出去这件事情了。
(译注:托翁的一封写给夫人的具有深刻意义的书信全文如下:
我的离家将使你感到悲哀吧。我觉得遗憾。可是,请你理解,请你相信:除此以外,我再也没有旁的办法。我在家庭里的立场正在变得很难堪。不,已经变得很难堪了。姑且把其他一切原因除去不谈,我在这一直过到现在的奢侈环境里,已经再也不能够生活下去了。但我要实行跟我的年纪差不多的老年人们通常所做的事情——为要使自己一辈子的最后几天在孤独和静寂当中过去而隐遁于世外。请你理解这一点,纵然知道了我的住所,也不要来迎接我。你来迎接我,只有把你的立场弄得更尴尬,决不能使我的决心改变过来。
我要感谢你跟我一块儿度过四十八年间的诚实生活,我要请你宽恕我对你所犯的许多罪过。因为我也由衷地宽恕你也许对我曾经犯过的一切罪过。请你适应那由于我的离家而开始的新境遇,不要对我怀着恶感。倘若有什么想要告诉我的,就请对沙夏讲吧。沙夏会知道我的住所,会把必要的东西送给我。但她不会说出我在哪里。因为她曾经跟我讲好:无论对谁也不说。
托翁这封信的草稿,实际上在头一天(二十七日)已经在笔记本上写好了。)
把朵香和沙夏喊了起来,他们两人帮我收拾行李。我想:她一听到,就会跑了出来,歇斯底里地吵闹一场,那就再也不能够悄悄地离家了。这么一想,我战栗起来了。快到六点钟的时候,总算把行李收拾好了。
我跑到马厩里去,叫他们驾马。朵香、沙夏、娃利亚也准备好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迷失了到旁屋去的道路,走进了树丛里面,身体被刺伤了,碰在树上,跌倒了,丢失了帽子,再也找不着。好容易从那儿跑出来,回到正屋里,重新拿着帽子,点着蜡烛,才走到马厩里,吩咐他们驾马。沙夏、朵香、娃利亚也来了。我期待着追踪的人,发着抖。但终于出发了。在希柴其诺等了一个钟头。
这期间,我不断期待着她出现。但我们终于坐进了车子里。火车开始动起来了。这时,我的恐怖忽然消失了,而生起对她的怜悯之情。
可是,自己是否做了该做的事情,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发生过疑问。也许是错了,在替自己辩护也未可知。
但我觉得好像被救了出来的并非列夫·托尔斯泰,而是那种虽然很轻微但却时时昭示我的内心的存在的东西。到了欧普齐那。我没有睡,也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但很健康。从葛尔巴柴沃起的旅程,坐的都是塞满了工人们的三等车。我的感觉很迟钝,但极其富有教训意义,也很有趣味。此刻是八点钟。我们在欧普齐那修道院里。
作者|托尔斯泰
译者|任钧
摘编|张进
编辑丨董牧孜
微博编辑|王易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