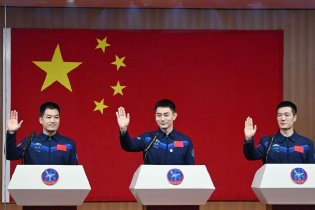原载《北京文学》2019年第4期
注:转载作品请与作者本人联系授权
链接:李燕燕:拯救睡眠(一)

睡眠对正常人来说就像呼呼喝水那样易如反掌,然而对于失眠的人来说却难如登天,失眠会让人百爪挠心痛不欲生,黑夜对他们来说就如地狱、噩梦,没有失眠经历的人是很难体味失眠的痛苦的。如此说来,人都害怕失眠,渴望正常的睡眠。然而失眠的人如何才能拥有正常的睡眠,正常的人未来如何不患上失眠?读一读这篇报告文学,或许你会觉得本文的题目并非危言耸听。
拯救睡眠
——谨以此文献给我国正在发展中的心理健康事业
李燕燕
心 病
同以往一样,宋大姐看完病就搭乘动车回石柱。这次,是在主城开副食店的三儿子“老三”开车送她去的火车站。老三的左脸还时不时有些抽搐,但已经算恢复得不错了。在宋大姐犯“焦虑症”前的半年,去批发市场进货的老三刚把肩上扛的一袋80多斤的干辣椒扔进小货车,突然晕得天旋地转,跌到地上怎么也爬不起来。送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突发脑梗,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很长一段时间半边身子“发麻”。老三才28岁,很年轻。“那样年轻就中风了,真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宋大姐很心忧。老三的媳妇负责看店,一有空闲就去打麻将。老三中风的时候,孩子刚刚两岁,宋大姐提出把孩子带回石柱去抚养,被老三媳妇拒绝了,理由是“镇上连个像样的幼儿园都没有”。那段时间,宋大姐睡觉常做噩梦。有一次梦见小孙子在燃起熊熊大火的副食店门前大哭,“半夜惊醒,脑子很乱,要一个多钟头才能平复。”
再难受,宋大姐也不会在外人面前表露半点,从年轻时就如此。她坐在蜀葵节节攀高围成的花墙里,大声跟客人插科打诨,笑呵呵地接受客人对她 “做农家菜地道”的赞扬;她穿一身花花绿绿,做事比村里的妇女主任还风风火火;家里年年创新高的收入和儿子儿媳的孝顺,以及读小学的孙儿孙女考的“双百分”,是宋大姐在村里人聚集时的最好谈资。随时随地,走路挺胸抬头。年轻的时候,因为村支书欺负丈夫老实,动了手,宋大姐闻讯赶上前,操根棍子犯了浑。几个大男人都拿不住她,因为这个女人不怕事。
“那个村支书亲戚多得很,家族有势力,我们势单力薄。我就横下心,不过就是拼命。”有一个星期,宋大姐出门都揣着一把菜刀,“说不怕也怕。但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
回乡镇的公交车上,她接到了大儿子打来的电话。大儿子是漆工,在广东做工,这通电话是在一个酒店的装修现场打的。电话里电钻隆隆,噪音很大。此时,身体微微发胖的宋大姐正被一个怀抱一只大包裹、沉沉入睡的大爷挤到座位一角。“我给屋头拉了笔业务,4家人6月中旬就会过来避暑,屋头可以预先作好准备。”老大特意嘱咐,每个客房都需要单独装个wifi,他上次回来发现二楼和三楼信号都很弱,这样客人不会满意。“哎呀,娃儿就晓得布置任务,都不晓得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不懂这些现代玩意儿,只有跑到镇上到处去找人帮着弄,麻烦得很。”挂了电话,宋大姐眉眼间悄然现出愁容。
二儿子的语音微信是一大早发过来的,但宋大姐当时忙着挂号看病开药一直没时间。直到夜里到家,连上wifi,她才打开微信。二儿子在广东另一个城市打工,他在时断时续的语音里讲,前两天媳妇刚刚做完一个复杂的妇科手术,还要住一段时间医院,花费很大。之前他们买了辆车,积蓄都投进去了,飞来横祸急需家里支援,末了叮嘱母亲要按时吃药,好好睡觉。宋大姐看看墙上挂的时钟,快9点了,一阵熟悉的心悸凭空而来。犯了关节炎的老伴瘸着腿从小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素面,搁着几片莴笋叶。
“老二家又出事了。”宋大姐叹气,随即抚着胸口发呆。老伴把那碗面搁到旧饭桌一角,搭了搭宋大姐的肩膀,“你先吃点东西吧。不要瞎操心,咱们不缺钱,明天我去镇上给娃儿汇款,事情总归会过去。儿孙自有儿孙福。”
老伴记得,半年多前,宋大姐凌晨3点胸口难受得在床上直翻腾——也是第一次犯病,正是白天接到二儿媳的电话,说老二带了一帮工友去找老板讨工钱,结果双方动手打群架,全部进了派出所,可能要拘留。
“事情坏就坏在我堂客她压根儿不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她活得仔细活得要强,得的是心病。”
年轻人在外讨生活不易,宋大姐常常念叨。
这几年家运屡有不顺,宋大姐从去年年初就开始吃素念经,祈祷平安。现在,宋大姐将一根从山上寺庙求来的红绳结挂在床边;每晚脱下的鞋子,鞋尖一定要朝向床外。据说这样可以避免邪物在夜间侵犯,得到没有痛苦和噩梦的好眠。
下午3点40分,重庆市渝北区某小学门口,狭窄的街道停满小车,铁栏前堆满人群,各异的神色中纷纷透出焦急。很显然,白发在攒动的人头中占绝对优势。几分钟后,紧闭的学校大门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缓缓推开,人群开始随之移动。放学时间到,63岁的老张跟随挤挤挨挨的人群,进入学校接孙子。几分钟后,老张背着书包,拉着8岁大孙子的手走出校门。可能城管马上要来了,路边摆菜摊的三轮车开始收拾、跑路。
“哎,等下!”老张喊住落在最后面、还在左顾右盼最后一单生意的菜贩,迅速挑拣杀价买下了平菇、莲白等几样小菜。接着掏出手机给老伴王大姐打电话。此时,王大姐正在家里看管半岁大的“二胎”。
“喂,老大接到了,菜也买好了,现在我马上送老大去艺术班学画画。给老二洗头洗澡的事儿,等到我回来,热水器的水温你调不好。”所幸艺术班隔得并不远,只有半站路。
老张和王大姐到重庆照顾孙子,前前后后已经有8年了。“原以为,孙子上了小学,我们就可以回家休息,哪知道老二又来了。孩子爸妈,一个公务员,一个在国企,哪里有空带孩子。亲家那边经常住院,保姆费钱又不放心,我们只有硬着头皮扛下。”
而老张和王大姐有“失眠”这个毛病快五年了。毛病是不知不觉有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张每天晚上最多只能睡“四个钟头”,在一番辗转反侧之后;而王大姐睡眠很浅,总是处在“迷迷糊糊半梦半醒”的状态。夫妻俩常常会相互埋怨,最多的是王大姐说老张:你能不能不要老翻身,你快两百斤的人翻下身,床很响,本来我快睡着也醒了。老张很无奈,不翻身一侧身子僵得疼。五年来,他们先是按照朋友的推荐吃维生素,“说维生素有催眠效果”,感觉作用不大。异地就医毕竟麻烦,手续繁杂,于是又拿着儿子的医保卡去社区医院开一些艾司锉仑——属于传统的苯二氮卓类,似乎要好一些了。社区医院年轻的“眼镜医生”,开药时甚至头都不抬,因为找他开这种药的人很多。这种药长期吃有药物依赖,肌肉松弛作用会导致老年人摔倒。但这些副作用恰好被这对老夫妻所忽视。
2015年,老张带着王大姐游古镇。四合院里,王大姐在抬腿跨过第二道门槛的时候,一只脚突然不得劲儿,脚尖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啪的一声摔一跤,结果脚腕骨折。许是年纪大了,休养了两年才慢慢康复,可是睡眠问题更突出了。
眼见大孙子磨磨蹭蹭进了艺术班的教室,老张轻轻吁了口气。回去的路上,他检视自己在游摊上买的小菜时才发现,西红柿上有块烂斑,老伴是要骂的——这两年老伴脾气越发不好,整天絮絮叨叨地抱怨,就仿佛在为缺失的睡眠寻找一个出口。况且,今天早起老伴心情就不好,她说梦见前年去世的老母亲,带着她去老家走了一圈,遇见的全是死了的“老辈子”。这是凶兆,王大姐一口咬定,今天已经不安地念了很多遍。老张还得去安慰她,再强调一遍世上没有鬼神。
“我俩其实挺孤独的。”提着小菜,老张露出落寞的表情。
由于不会说四川话、不适应巴渝风俗,“连麻将打法都完全不一样”,在这里几年下来,老张王大姐的朋友圈只有儿子儿媳,能称得上点头之交的邻居只有两三个,“其实有一个挺谈得来的,跟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可老伴不喜欢她,说老了老了还涂脂抹粉,妖艳。”这个社区十多栋楼里住了上千人,虽然一早一晚老两口都会在小区花园遛弯儿,但对老张和王大姐来说,基本都是陌生人。“现在不像以前,家家户户门都关着,谁也不理谁。哪像原先80年代的平房闷罐房,小归小,成日家门都是打开的,邻居之间互相串门。”生活没有任何动力,只有在面对两个孙儿的时候,他们才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儿子儿媳下班回家后,老张常常感到很失落,“他们下班回来,要么看电视、玩手机、逗孩子,要么在家继续加班,反正不大跟我们说话。我理解,他们白天忙了一天,回来不想说话也正常。”
在中国,像老张王大姐这样“给儿女帮忙”的随迁老人还有很多,他们被称为“老漂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城市“老漂族”不断壮大,是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也带有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区隔的特点,同时反映出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合理性和隔代育幼的现实性。但不可忽视的是,老人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随迁老人”面临“不适应”“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不适应主要集中在环境气候、语言交流、风俗习惯、人际交往等方面。家族成员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可能加剧,随迁老人的心理问题,包括睡眠障碍便会凸现。
失眠已久、脾气大变的王大姐,对儿媳的生活习惯已经发展到“忍无可忍”。看不惯儿媳周末睡懒觉啥都不干,看不惯儿媳连自己主卧的马桶都不拿洗涤剂擦干净,看不惯儿媳没事喜欢买买买。跟儿子说几句,儿子却向着媳妇说话,反而劝她不要干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每每爆发激烈的争吵,王大姐都想直接撒手回老家了,说不定回家就睡得着觉了,却又舍不得两个孙子。
在这个周边生活还算便利的社区里,随迁老人几乎都来自区县和外省市,其中农村、乡镇占了一半,照顾晚辈的更占到了70%。不容忽视的是,“失眠”成了随迁老人的“通病”。
“睡不着,想家。家里院子种的橘子树每年都结很多果子。”
“我想要的很简单,在自己的家里,吃点自己种的小菜,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老张说:“我和老伴真想回老家,去过一段真正退休后的日子。旅游,走走看看,见见故乡的朋友。现在再不走动,以后想动也动不了了。”
夜里11点,老张夫妻开始辗转反侧的时候。57岁的况老师终于做完了所有上床前的“仪式”——躺下,平卧,放空大脑,祈祷尽快入眠。
每晚的睡眠对于作家况老师来说,非常重要,又异常艰难。他已经吃了10年会导致药物依赖的阿普仑。从晚上10点开始,是整整一个小时的“上床准备”——
先在跑步机上运动20分钟,速度不快不慢。
拿出女儿从国外带回的红酒,在高脚杯里倒上半杯,绝对只能半杯。一年前况老师尝试喝酒助眠,对酒精寄予厚望。虽然并不科学,却是有理由的。年轻时况老师与文友们相聚,几杯白酒下肚,回家倒床就睡。喝酒助眠,一开始喝一点就管用。两个月后,每天都喝,喝到一瓶红酒或四瓶啤酒的程度才勉强见效,反而伤了肝。“酒是好东西,但一定要控制。”况老师跟朋友说。
读诗、读散文,欢快的积极的那种调子,大声读出来。
给大鱼缸里的金鱼喂食,然后欣赏一会儿。
吃药,上床。
况老师没有想到的是,所有的“仪式”都只是“楼上掉落的一只靴子”,“另一只靴子”还迟迟没有动静。况老师保持平躺放空大脑,一个小时过去了,并没有如愿进入睡眠状态。凌晨一点,门锁被钥匙转动的声音终于传来,咔嗒咔嗒,夜深人静之时格外清晰。女儿小真终于回来了。
小真轻手轻脚地点开鞋柜之上的小灯,小心翼翼脱下高跟鞋。动作还在进行中,客厅的吊灯陡然亮了。扭头,父亲已经铁青着脸靠在沙发旁。
“为什么又回来这么晚?”
“早上走的时候就说了,晚上要加班。”
“加班?是跟朋友瞎玩去了吧?有这些时间,不如多看看书,考个研或者考公务员也好,你那个工作不靠谱。”
“爸,别太专制了!”
“我是关心你。”
凌晨一点半,父女俩再次发生争执。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凌晨3点过,况老师入眠了。零碎的梦境里,他正在给幼年的小真改作文。《我爱蚕宝宝》,文笔还是嫩了点,不够优美。算了,还是我来替她重新写一篇吧,肯定能在全国拿一等奖。
24岁的小真一直觉得父亲想要全面“掌控”自己,以“关心”为名。比如,雨天堵车,她赶不及回家吃晚饭,便先打个电话告诉父亲。挂掉电话不到两分钟,父亲又打了过来。公交车停靠站台,大雨滂沱,小真忙着撑伞,就没有接这个电话。回家后父亲动了怒,大声责怪她不接电话,因为他有很重要的事情交代——“如果你坐的是465路,那它会在轻轨站的前面20米左右停,你下车可以径直走进轻轨站,然后穿过通道从另一侧上来。”这段充满“父爱”的“交代”,让常常在国内外飞来飞去的小真哭笑不得,“父亲有时不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况老师觉得女儿越来越“把控不住”了,他很担心。他希望一切“可控”,虽然近20年来,太多的事都“不可控”。当年该他晋“正高”,硬件软件资历一切合格,中途却杀出单位的“引进人才”;妻子温柔敦厚、心性纯良,有人告诉他看见“他爱人和别人很亲密”,他不以为然,不到半年便接到妻子递来的“离婚协议书”,妻子连女儿都不要;他的中篇小说已经过了某政府奖的终审,却突然有人举报他“抄袭”,“抄袭”的是“结构”,虽然调查未果,可是获奖的事也彻底黄了……从过去的经验看,女儿相对可控,现在也未必。
今年6月,由于严重失眠及巨大的不安全感,况老师被迫到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就医,在诊断出中度抑郁的同时,还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的迹象,被医生建议作进一步检查。
当前,老年人的睡眠问题突出且带着较大风险。陆林院士课题组研究发现:一、在自我报告存在睡眠障碍的老年人中,抑郁症发生的风险显著增加,且持续存在的睡眠问题会加剧老年人抑郁症的发生、复发和症状的恶化。另一方面,具有抑郁症状的老年人睡眠障碍的发生和恶化的风险也会增加。二、失眠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充足的睡眠有利于脑保护,有利于降低发生老年性痴呆的风险。
老张夫妻所在的社区里有很多新生的婴儿。夜里常常能听见婴儿们的哭声,此起彼伏。随迁老人和新手妈妈多的现象引起了社区的重视,2017年初,社区便向重庆市某社会服务中心购买了包括心理咨询、社会融合等一系列服务。
从事心理救助的社工陈琼在这个社区里遇见了一位新手妈妈,对方才张口说了几句话,便哭了出来。这位看上去非常年轻的妈妈大哭着告诉陈琼,自己的女儿只有4个月大,睡眠问题非常严重,每天会夜醒“无数次”。这位新妈妈指着自己明显的黑眼圈和满布血丝的双眼,大喊:“救救我,我快崩溃了!”按惯例,陈琼让她用涂睡眠时间表的方式,记录孩子每天的睡眠和苏醒时段,拿到妈妈的反馈,陈琼被其记录的详细和精确惊到了,比如: 7点起床,凌晨2点第一次夜醒,吃奶瓶5分钟,玩耍3分钟,小便1分钟……焦虑化为一串串数字显现在表格中。
“甚至在某些夜醒的点,可以看出,她是在期待这些,预知这些不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然后真的发生了,有点墨菲定律那种感觉。”陈琼觉得很有意思。在深入交流中,陈琼进一步发现,这位妈妈所理解的“夜醒”,有时根本只是孩子“翻了个身”或是“呢喃一句”,这些本是正常现象。但由于“可能是夜醒”的不安,新手妈妈便对孩子的睡眠进行干预,反而把孩子吵醒。“夜醒”成了事实,孩子客观上存在了“睡眠问题”。
在西方婴幼儿睡眠的跨文化研究中,阿维·萨德与约迪·明德尔等人2011年发表的论文,比较了西方社会与亚裔社会中父母对孩子睡眠问题的感知,结果显示,后者认为孩子有睡眠问题的比例是52%,其中17%认为问题严重,显著超过前者26%(其中2%严重)的比例。
对婴幼儿来说,究竟怎样才称得上“睡眠问题”?陈琼倾向的判断标准是,当孩子的睡眠已经影响到大人了,就应当寻求帮助。
6年前,陈琼还没有考“心理咨询师”,和这位新手妈妈一样,二十出头全职在家,一度因为孩子的睡眠而濒临崩溃。
“在中国,一直存在‘一切以孩子的需求为重’的家庭观。如果一个妈妈做了全职太太,那么就很容易在带孩子这件事上钻牛角尖——因为这是‘我’的价值最大的体现。”陈琼说。
陈琼当年做完剖腹产手术后大出血,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医生要求她“夜里保持充足睡眠,不要带孩子”,但她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婆婆从她怀孕辞职在家开始,就利用各种机会敲打她:“男人在外面挣钱养家不容易,他主外你主内,你最大的事就是带好小孩。”虽然对婆婆的话心有芥蒂,但小孩落地,陈琼就开始和自己较劲:我一定得是个特别尽职的妈妈。事必躬亲,做到极致。孩子半岁的时候,1.65米的陈琼一度瘦到只有80斤。
有人曾打趣说哺乳期的妈妈是“24小时型人”,与常见的作息节律分类“晨型人/夜型人”不同,妈妈们“不需要睡眠,全靠一口仙气吊着”。新生儿父母,在责任感的召唤下,成为睡眠被剥夺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接触专业的婴幼儿睡眠知识后,陈琼开始反思“一切以孩子需求为重”的“家庭观”。“若大人因为睡眠剥夺无法保持平和的情绪和良好家庭氛围,孩子不可能不受影响。”她相信,孩子不过是家庭成员中的一分子,只有每个成员的重要性平等,才可能真正彼此尊重。
冰山之下
……


李燕燕,笔名燕子,女,1979年10月出生于四川成都。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主要从事报告文学及散文创作。在《北京文学》《中国报告文学》《神剑》《前卫文学》《重庆文学》《光明日报》《文艺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重庆晚报》等报刊发表报告文学、散文作品近50篇。出版报告文学集及长篇纪实文学共两部。获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等项目资助。
链接:这本由老舍先生在1950年创办的杂志——2020等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