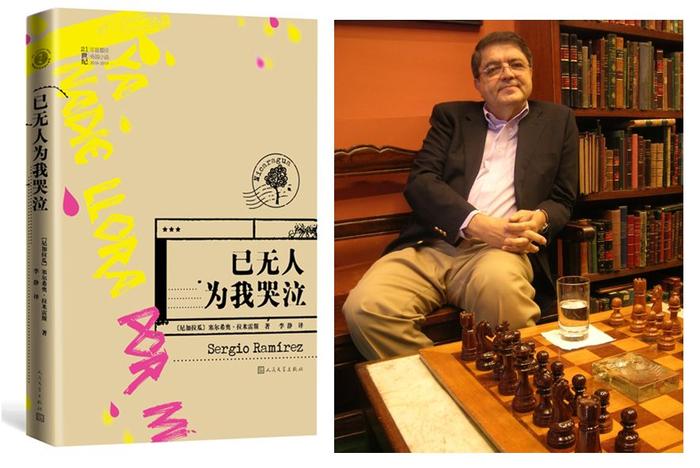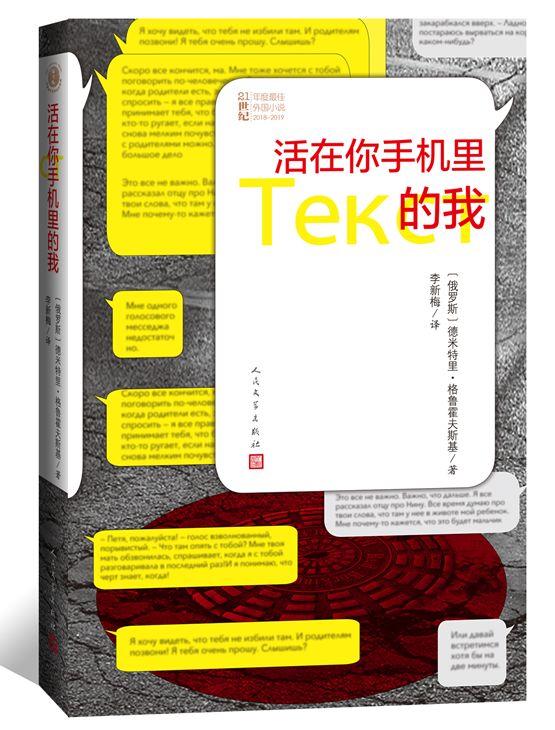
俄罗斯当代作家格鲁霍夫斯基的《活在你手机里的我》描写了被冤入狱的主人公伊利亚刑满后回到故乡,却发现已经回不到过去的生活,复仇之后他拿着落在他手中的死者的手机,充当起了死者。当几乎可以成功逃离一切时,他又面临艰难的抉择……
该书入选2018-2019年度“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给这部作品的颁奖词是:
俄罗斯当代作家格鲁霍夫斯基的《活在你手机里的我》是一部现代版的《罪与罚》,由无辜的获罪和非法的惩罚构成的小说情节起伏跌宕,扣人心弦;相继扮演两位男主人公“第二自我”的手机则构成一个关于当代生活的巨大隐喻,即人类生活的“文本化”以及“文本”作为人的“双重人格”的存在方式及其悖论内涵。

该书作者德米特里·格鲁霍夫斯基,1979年生,俄罗斯当代畅销书作家、记者。毕业于耶路撒冷大学新闻和国际关系系,主要作品有《地铁2033》(2005)、《黄昏》(2007)、《地铁2034》(2009)、《未来》(2013)、《地铁2035》(2015)、《活在你手机里的我》(2019)等。入选2018-2019年度“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四部小说,将有一本入选“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昨天,我们分享了《首都》的节选(点击蓝字可查看),今天,我们便推出其余三部作品的试读篇章,下面便是《活在你手机里的我》节选。希望您能读过书后参与本次投票!投票方法:请读者朋友在阅读候选图书后,于2020年1月10日24:00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官方微信、微博上公布的投票平台上进行投票,并撰写评语。2020年1月11日—15日,我们将结合两组投票结果(专业评委选票权重60%,读者选票权重40%),选出2018-2019年度“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获奖作品,奖金人民币5万元。我们还将根据读者的投票结果及其撰写的评语,评出最佳参与读者奖:
一等奖一名,获5000元奖金。
二等奖三名,每人获2000元奖金。
三等奖十名,每人奖励价值1000元的图书。
扫下方二维码,或点文末“阅读原文”即为投票地址
《活在你手机里的我》节选窗户映照出十一月苍茫的暴风雪以及模模糊糊的云杉。电线杆像黑白电影里的镜头一幅幅滑过,让人眼花缭乱。窗户映照出的俄罗斯,与从索利卡姆斯克索利卡姆斯克是俄罗斯彼尔姆州第三大城市,位于中乌拉尔山西坡,卡马河中游卡马水库北端。延伸出来的那个俄罗斯一模一样:同样有云杉、白雪、电线杆,接着是林中空地中歪歪斜斜的木屋、火车站以及看起来像缺乏维生素的两层砖墙小楼,同样是——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的云杉,它们矗立在道路两旁——像铁刺缠绕,让人无法通行。但在窗外这个广袤无垠、千篇一律的俄罗斯自然造物里,隐藏着它所有的实力、雄伟和魅力。真他妈的美啊!“你打算做什么?”“我要活着。你呢?”“我想杀了他。”“嗯。可我原谅了他。我现在想活着。可以再借用一会儿电话吗?妈妈不知为啥没接。”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弥漫着新鲜空气和内燃机炉渣混合而成的浓烈气味。当你闻过卧铺车厢里的酸腐味,火车连廊里的烟熏味、铁皮味和甜腥的尿液味后——这里的空气实在太充足:氧气过量,一下子像浓茶一样浸润大脑。莫斯科也是如此,它在云杉道的尽头像浩瀚的宇宙一样对外来者敞开胸怀。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们跳出车厢,跨过沟壕来到站台,卸下用胶带捆扎的中国式方格旅行箱,然后双手将它们抓住,沿着月台往远处四散而去,就像强击机沿机场跑道起飞一样。远处烟雾朦胧,迷雾中的宫殿、城堡和高地,都向外来的人们散发出微弱的光芒。伊利亚比谁都不着急,他在人流中无须用力——随波逐流即可。他嗅着莫斯科的天空,时不时地抬起有些生疏的双眼看看远方,暗自吃惊。外面很亮,像童年时一样。十一月阴沉的莫斯科刺得他眼睛发痛。他到莫斯科了,但还没进城区。火车站还只是在郊区,它污渍斑斑,像被油盐浸过。不过,就像孟加拉国使馆不管怎么说都属于孟加拉国领土一样。站台的尽头设有通行检查。伊利亚习惯性地越过别人的脑袋远远看见了岗哨。灰色的制服,油腻的嘴脸。锐利的双眼在搜寻着,似乎能一眼看穿。这个,这个,这个。甚至有拴着链子的工作犬:与警犬一模一样。但显然,它不是真正的警犬。也许只是嗅嗅毒品、炸药之类的东西。但它可是能嗅出恐惧的。伊利亚开始眼望空处,避免遇到别人直勾勾的目光,也避免自己盯着别人看。他开始什么也不想,避免流露出任何迹象。“年轻人!”他立刻顺从地呆立在那里。他们怎么认出他的?根据皮肤的颜色?驼起的背?或者低垂的头?就像狗识别出野兽那样?“请过来。出示证件。”他递上护照。他们翻到备注页,呵斥着问话。“从哪儿回来的?”撒谎还是说真话?他们是不会检查的。我就说自己去了……去了某地。休假。去奶奶家。出差。他们怎么检查呢?“服刑了。执行判决。”“释放证。”他们立刻换了一种口气和他说话。主人式的。他掏出证件。中尉拿着证件转过身子,朝无线电台嘀咕着,同时听着那边的答复;伊利亚默默地站着,没有争辩。他清白无辜。从头到尾服满了刑期:曾被拒绝假释。“改造好了,伊利亚·利沃维奇?”中尉终于转向他,但没归还证件,不知为何将其对折起来。莫斯科在中尉的背后越来越远,缩成一团,天空也越来越狭小,卷了起来。人群的喧闹声和汽车的轰鸣声渐渐平息。中尉及他的大肚子、油迹斑斑的胸膛、丑陋的嘴脸,取代了整个莫斯科。伊利亚似乎知道:他什么也不会对他做。只是想让他感觉到他有权力。那样他会舒服一些,也就会放了伊利亚。他现在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力,他正是为了这个才来上班的。“是的,长官。”“回居住地?”“回洛勃尼亚。”“户口地址是?”“仓库大街,六号。”中尉查了护照,毫无必要地将备注页揉得皱皱巴巴。他可能与伊利亚年龄相仿,但肩章让他看起来更老一些,尽管伊利亚——而不是他——这七年来每一年过得都顶三年。“你是回家呀。你有这个权利。”他哼了一下,“第二百二十八条即俄罗斯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他读完后说,“第一款。是什么?第一款。提醒我一下。”“准备。销售。我只是准备销售而已,长官。”伊利亚看着他下巴下方一点的位置——这是个特别的位置,谈话时应当看着工作人员的这个位置,不能盯着眼睛或地板。这个混蛋在拖延时间,他喜欢让时间为自己折腰,就像他折弯铁丝一样。突然工作犬开始朝着一个疲惫不堪的塔吉克人狂叫,这个塔吉克人带着像所有人那样的方格包。“好了。不要忘记去登记,”中尉把证件塞给伊利亚,“而且以后别再做生意了。”伊利亚点了点头,走到一边,把证件收进自己温暖的衣服内袋里,刚才被盘问时,他本人也想藏进这个口袋。中尉已经开始忙着盘问塔吉克人了,塔吉克人更有希望。他通过检查了。受挫的世界逐渐恢复知觉,开始有了声音。但现在,当伊利亚接近莫斯科时,他满眼全是从远处的火车上看不见的民警。火车站的广场上,地铁站的入口处,汽车站的小亭子里。一群一群,全都长着警犬一样的眼睛。不过,问题可能不在于莫斯科,而在于伊利亚本人。他是夏天被带走的,秋天结束时获释。他被释放时的莫斯科,不再像他被带走时的莫斯科。莫斯科现在就像十一月光秃秃的树——湿湿的,黑黑的;以前莫斯科到处是鲜艳的招牌和售货亭,里面什么都有——现在它变得严肃了,从身上抖下花花绿绿的东西,变回到原样。可伊利亚喜欢以前的莫斯科,那时它像一个闹哄哄的大集市——他觉得他能在这个集市上为自己买到任何未来。那时他每天乘电气火车从自己的家乡洛勃尼亚来到莫斯科——来到学校、俱乐部、音乐会——而且每次他都将自己想象成莫斯科人。他只需要念完书,在市中心找到工作,然后和朋友们一起租房。莫斯科的土地很神奇,它富含生长激素:只要你往里面塞进自己的欲望——它们就会生长,然后你就会有带薪水的工作、时髦的朋友、最漂亮的姑娘。莫斯科善于自我陶醉,并善于将自己的陶醉分享给所有人。在莫斯科一切皆有可能。即使伊利亚从它那膨胀的甜面团上揪下自己的一小块幸福,莫斯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而现在它仿佛在他的梦里——在牢区时,他可是总梦见它。它现在变得更严厉,更光洁,更严肃,更官方了——也因此看起来像人们周一因周末喝醉酒而得了后遗症那样。他辨认了半天也没认出它。感觉自己在这里是个异乡人,是个旅行者,是个来自索利卡姆斯克的旅行者,而且还是来自过去。他在三个火车站的公共广场上站了一会儿。站在其他同样发愣的外省人中间,他这个来自牢区的外来者已经不那么显眼了。可以做做深呼吸,还可以眨眨眼。他眨了眨眼,开始前行。他小心翼翼地踩着莫斯科的土地,以免它因为他幅度过大、为时过早的脚步声而真的成为消失的梦境;以免自己醒来时发现它已离去,而自己穿着像画布一样粗糙的灰色监狱服,待在冰冷的、不透气的、散发着臭袜子味的营房中,躺在架子床上,躺在命运陷入死胡同且时时刻刻担心自己犯错的人中间。但莫斯科坚实地矗立在那里。它的确在那里,而且永远在那里。他被释放了。的确是被释放了。伊利亚用剩的不多的钱买了地铁票,然后走向地下。迎面而来的是电梯从地下送上来的莫斯科人——可以好好看看他们的脸了。七年里人们的穿着变好了,就连塔吉克人也是。人们坚定地望着上前方,很多人无法忍受等待半分钟而选择爬楼梯:出了地面有很多急事要办。伊利亚想起来了,莫斯科人的生活总是忙忙碌碌。而牢区让人没有时间概念。在迎面而来的人群当中——有相爱相拥的老人,有在手机里听过的流行歌手,有不屈服于年龄的朋克——伊利亚唯独害怕女人。这些年他已不习惯女人了。他似乎忘了她们如此非同寻常,比常人要漂亮得多!而且假如她们中的某一位突然回应伊利亚的目光,他会追随她的诱饵,而她将吸引着他反道而行——让他跟随自己,上到地面。然后有一个女人皱了皱眉,无声地抽了抽鼻子,伊利亚立刻蔫了,蜷缩起来:她们肯定能看出他不久前还是个囚犯。仿佛他的额头上刻有灰蓝色的囚犯的文身,土黄色的皮肤也说明了这一点。他身上的衣服像粗布工作服。女性能在男性身上嗅出危险,嗅出饥饿和不可靠——这是她们身上的兽性,永远不会错。伊利亚继续时不时地偷偷打量她们,有点拘谨,生怕谁会再次揭穿他。他偷偷打量着——而且情不自禁地在每个女人身上寻找维拉的影子。他决定无论如何也不给维拉打电话。原谅她的一切,但不给她打电话。打电话对他毫无用处,即使她同意通电话。只是听听她的声音吗?有什么必要?他自己已经无数次变换角色替她说出了问题和答案、劝告和责备。他想象中的维拉总是避而不答。真正的维拉已经通过一个电话向他解释了一切,那是他入狱后的第二年。她道歉,竭尽所能忏悔。说自己不想撒谎,说自己遇到了一个人,说她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她不停重复这句话,就好像伊利亚和她争论似的。而他和她从来没有当着别人的面争论过。她一次也没看望过他。因此他是在同想象中的维拉争论——而且是五年。即使在想象中他也无法让维拉回心转意。在地铁车厢里他可以毫不畏惧地看着人们,甚至是坐在正对面的人。车厢里谁也顾不上他:全都沉浸在自己的手机世界里。全都在滑动屏幕:涂脂抹粉的大妈们用染过的指甲,斜眼的外地劳工用老茧,中学生用细如火柴的手指。所有人在玻璃屏幕里面都有另一种更有趣更真实的生活。以前智能手机是给赶潮流的人用的,给年轻人的。而伊利亚坐牢的这几年,网络变得像怪兽一般,老人也用,乳臭小儿也用。他们的牢房里只有一部手机。当然,不是伊利亚的。伊利亚不得不用妈妈转交的包裹里的香烟作为交换,打几秒钟电话,上几分钟VKVK是俄罗斯的社交软件。。包裹掏出时,钱会立刻被没收,而香烟减半——这是纳税。打电话非常贵,所以先听几秒妈妈的声音,然后留几分钟逛逛维拉的网页——时间很少。虽然维拉几乎不往网上放自己的照片,只放一些视频链接,或个性测试等无聊的东西。也许她明白,伊利亚正从监狱里注视着她,而她不想让他看见。伊利亚有时竟然还能省出一点时间看看狗崽子。看他那里的情况。看他的生活。看他晋升到了什么职位。看他在泰国的休假。看他在欧洲的样子。看他为自己买了一辆啥样的“英菲尼迪”。看他抱着什么样的姑娘。狗崽子的生活光鲜亮丽。每当看见狗崽子的照片时,他的嗓子像被钩子挂住了一样发痒,心像被刀刮一样痛。他看不下去——却又无法不看:仿佛是另一个人在替他生活一样。伊利亚的话费不够用来关注世界上的其他内容。牢区里的生活,只能别人欠你的,不能你欠别人的。没关系,他习惯了没有手机。尽管入狱前他一直幻想有一部手机,甚至提前一年向母亲预定了手机作为生日礼物。每次到学校上课时,他就把它放在课桌上,以引起姑娘们望着屏幕长长的对角线时的欢呼。这还不是他在那里不得不适应的主要东西。他在萨韦洛夫站出了地铁。又是民警。到处是民警。成千上万辆汽车缓缓地驶过三环,车灯白天也亮着,车轮下的脏泥被甩到空中,人流从地下通道喷涌而出,莫斯科在痉挛,在喘息,但还活着。伊利亚很想触摸它,想触摸一切,抚摸一切。七年来他一直想触摸一下它——莫斯科。“我到洛勃尼亚。”电气火车变化很大。他记得以前的电气火车是脏兮兮的,绿绿的,玻璃上有划痕,车厢两侧画满涂鸦,安放着公共木长椅,地上满是瓜子壳,洒出的啤酒慢慢挥发,于是所有的东西都散发着啤酒味。而现在是白净的新车,车体上有黄箭头形状的标志,座位是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乘客们彬彬有礼地坐在那里。白净的列车让他们变得高尚起来。“想不想和我一起去看娜芙卡这里指塔吉亚娜·亚历山德拉·娜芙卡,俄罗斯花样滑冰运动员,曾多次获得国内外花样滑冰冠军,个人生活绯闻较多,第二段婚姻嫁给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普什科夫。?滑冰秀。”一个疲惫不堪的大妈对另一个大妈说,“我在那里看过仙境剧。”“也许去。娜芙卡是不是嫁给这个人了,长着小胡子,是吗?这人是普京的秘书。不错的男人,仪表堂堂呀。”那个大妈回应道。她五十多岁,疲惫不堪,但脸上的粉涂得像灰泥一样厚。“得了吧,”第一位大妈摆摆手说,“娜芙卡本来可以选个更好的。你知道我喜欢谁吗?拉夫罗夫。拉夫罗夫不错。要是我的话,就选拉夫罗夫。他比你那个络腮胡更果断。”伊利亚听着,但什么也不明白。火车缓缓前行。空肚子咕咕叫,胸口隐隐作痛。他舍不得花钱买火车站的羊肉馅饼:小摊上的价格是莫斯科的消费标准,而他的路费却是索利卡姆斯克的标准。很快就能喝到妈妈做的热汤了,有什么必要花钱买羊肉馅饼呢?他很想喝妈妈做的汤。三天才出味道的那种。带酸奶油。像童年时姥爷教他的那样,往里面弄点干面包。蘸点汤,让面包皮在汤里融化,但不要弄化面包瓤,而要让它保持脆脆的,先闻闻菜汤——然后不顾烫嘴,舀一勺倒进嘴里。他开始流口水。而妈妈可能会面对着他,坐在角落里那个半米长的小桌子后面——也许还会号啕大哭。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呀。他入狱后的前四年,她每六个月就要去他那里一趟:她把从工资里积攒的钱全花在去索利卡姆斯克的路费上,花在为见面住的宾馆上。后来她得了高血压,伊利亚似乎也住惯号子了——就开始劝她不要再来了。他们开始电话联系,尽管妈妈还是不停地来。而最近一年他们的谈话通常以眼泪结束。尽管没什么可哭的,与已经服过的刑期相比,现在几乎不算什么了。可是他能对她说什么呢?旁边有狱警,或者更糟,有盗贼——伊利亚正是从他那里买来与妈妈通话的机会。所以,只要她一开始哭,他就立刻制止。没有其他办法。她明白这些吗?没关系,今天就让她哭个够。今天可以哭。一切都结束了。“洛勃尼亚站!”电气火车停在一条道上,另一条道上停满了货车,绵延至地平线尽头:那是些装满了石油制品的油罐车,上面结了霜。白霜上有手指画的标记——《我们的克里米亚》《奥巴马——废物》《14/88》《维塔利克+达莎》《我的家乡——明斯克》,等等。伊利亚一边走向过道,一边机械地读着。克里米亚事件发生时,伊利亚还在牢区,所以这事就与他无关了。牢子里的人对克里米亚很漠然,狱警们的国家抢来的东西不会让他们心动。牢子里的人——按照定义就是反对派,因此号子里不会给他们选举权的。伊利亚决定从车站走回家。第一次需要徒步走过整个路程。他想这样。而且这比等公交车快。洛勃尼亚的天气与莫斯科完全不同。莫斯科闷热,空气因汽车尾气变暖。而洛勃尼亚的空气更明净,更寒冷,天上还飘起了寒冷的雪花,扑打在脸上。人行道上的雪还没融化,柏油马路上到处是被踩实的雪。汽车上沾满污渍,轮子搅动着暴风雪及其混杂物。单元楼直直地矗立在那里,被风吹得粗糙不堪,看起来很阴郁。人们的戒备心更强了。浓妆艳抹但脸色苍白的女人们行色匆匆,裹着连裤袜的双腿冻得冰凉。电气火车离开莫斯科总共才半小时,但伊利亚仿佛来到了索利卡姆斯克。七年里莫斯科变老了,洛勃尼亚却一点也没变:还是伊利亚被带走时那样,还是他童年时的模样。所以,在洛勃尼亚伊利亚感到很亲切。他从列宁大街拐到契诃夫大街。那里有三条横切大街:契诃夫大街、马雅可夫斯基大街、涅克拉索夫大街——它们的一边紧靠着列宁大街,另一边靠着工业街。契诃夫大街上有妈妈的学校,第八中学。妈妈的学校也是他伊利亚的学校。她当然把他安排到自己的学校了,尽管在自己家的旁边——几乎就在院子里——有另一所学校,第四中学。那里原本更方便一些,更近一些,而小孩走到第八中学需要半小时。但妈妈还是把他带在自己身边。七年级之前他们每天一起去学校。之后女孩子开始嘲笑他,于是伊利亚开始比妈妈提前十分钟跑出家门,以证明自己的成熟和独立。也是那时他开始抽烟。在学校大门的对面,伊利亚呆住了。还是黄白色的三层单元楼,还是像孩子们画房子时画的那种三格子窗户——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学校一样。它似乎在最近二十年一次也没修缮过,仍旧为伊利亚保持着早先的模样,以便他能轻松地回忆起一切。他深呼吸了一下。看了看窗户:二楼有一些小孩跑来跑去。是延时生延时生指放学后因为没人接而延长在校时间的小学生。。时间是下午三点。妈妈已经离开学校了。假如火车提前到的话,他就可以直接在栅栏旁迎接她。然后一起踩着雪回家,就走平时的那条路——沿公路,横穿过道。但那样也许会有其他女老师和她一起出来。比如教务主任,那个阴郁无聊的女人。她们一定会认出伊利亚,尽管他皮肤土黄,头发被剃掉了。她们曾经往他头脑里灌输了多少年的字母和数字呀……她们一定会认出他的。那样该怎么办呢?妈妈是如何向同事解释他入狱的事的?像他给她解释的那样?她很相信儿子:不相信儿子是吸毒犯兼毒品贩子。可学校里的这些大妈……她们没有必要去相信他。当面——她们会点点头,打哈哈,可背后呢?他出现在她们面前会不会给妈妈丢脸?她们会同他打招呼吗?他会同她们打招呼吗?伊利亚把手伸进口袋,愁眉苦脸地继续匆匆前行。其实是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晚些时候再和他们所有人见面,等到想好说什么,想好如何介绍自己时。迟早会见面的。毕竟洛勃尼亚是个小城市。他沿着工业大街两旁的俄式混凝土栅栏走到布基诺大道,然后顶着风雪沿着路边前行,时不时地打滑,但没摔倒。莫斯科财经政法大学在雪中微微泛光,维拉曾在那里读书。在二十七号楼的旁边,他再次停了下来。是维拉家。这是一幢十六层的灰色大楼,带黄色玻璃敞廊——人们称其为阳台,其实那就是再多弄一两平米的空间。伊利亚数到七楼。他很想知道,维拉还住在那里吗?或者已经去莫斯科了,就像她曾经打算的那样?她现在已经二十七岁了,和伊利亚一样。未必还会和父母住在一起。那里总共有三幢像维拉家那种脏兮兮的、用预制板盖成的十六层楼,它们独立建在一大片地的边缘上。它们的底部紧贴着一幢不大的漂亮砖房,很像自建房:这是一座与这里的风格完全不搭的剧院。二楼以上的地方不知为何用巨大的哥特体写着——“室内演出”。伊利亚瞟了一眼。歪着嘴对这个旧称的新含义笑了笑。“室内演出”的俄文是“камерная сцена”,这里的“室内”(камера)在俄语中还有“囚室”之意,伊利亚看见后立刻联想到自己在监狱里的“囚室”。剧院一直在那里,名称也一直如此,从伊利亚记事起就如此,不管他来这幢房子接送维拉多少次都依旧如此。上演的剧目有:《偶像》《一个男人来到女人这里》《五个夜晚》。新年很快就要到了。他蜷缩起身子。在用预制板和砖头搭建起的布景中,他那原本模糊的过去以饱满的色彩呈现出来。回忆太过清晰,而他原本不想如此。十年级时的四月份,他邀请维拉来到这里。来看《聪明误》。他得到了父母的允许。整个演出期间他抚摸着她的膝盖,听她如何喘息——断断续续。听着听着,心神荡漾,心儿颤抖不已。演员絮絮叨叨的内容都听不见了。可维拉挪开他的手掌,然后以十指相扣回应他。她的香水很甜,带着某种浓烈的香料味。后来他才知道:这甜美鸡尾酒般的浓香——是维拉自己的,是她的体香。给我马车,马车。这是格里鲍耶多夫的剧本《聪明误》快结束时的一句台词,表示伊利亚在剧院一直无心看戏,戏结束时才听到最后一句台词。然后在入口处他粗鲁地吻了她。那里散发着猫和暖气的味道:非常舒适。她舌头的味道与他自己舌头的味道很相似。接吻完全不像书上写的那样。下腹痒痒的,为此他感到非常羞愧,却无力停止。维拉在耳边私语。当她的父亲从七楼朝着旋转楼梯大喊一声后,伊利亚用钥匙在那里刻下两个词——维拉+伊利亚。也许,这个表白从那时起一直没有消失。她每天经过那里——还吐唾沫。假期过后,他们都是成人了,她邀请他到自己家做客。父母不在。她说,咱们做功课吧。沙发是条纹布的,被压坏了。体香,的确不是香水。屋内很亮,光照着很不好意思。地板上有半瓶两公升装的芬达。然后他们——大汗淋漓,空着肚子——轮流贪婪地喝着刺舌的橙黄色液体,之后互相望着对方,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后来呢,后来继续那样过了三年。他们住在一起。伊利亚眯着眼看了看她的阳台,看了看窗户:那里是否有人影晃动?看不见。而且维拉也许不住那里了。去了莫斯科。阳台空荡无语。玻璃模糊不清,后面是——自行车,各种腌菜罐子,维拉父亲的鱼竿。他横穿过道,继续沿着布基诺大道前行,希望在覆盖着积雪的幽暗大道上想象夏天,想象他和维拉曾经如何沿着这条路线散步。但想象不出来。相反,“天堂”里的画面固执地浮现在眼前,像烟雾一样挥之不去。那个夜晚。舞池。狗崽子。一切的一切。画面不断浮现,像烟雾一样腐蚀双眼,甚至让人流泪。那时他做的一切正确吗?正确吗?正确吗?而她之后呢?不管怎样——都是正确的?没什么。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这七年很快也会被遗忘。生活会照旧。他没走左手边的洛勃尼亚街心花园:高压线巨大的底盘的台基旁有四张长椅围成长方形,不远处有一片小白桦林,但因靠近高压线而枯萎残败。尽管冰天雪地,但仍有推婴儿车的妈妈们坐在长椅子上,她们守护着婴儿车,想让孩子多呼吸呼吸氧气。他拐到炮兵连大街。他走过炮兵连纪念碑,这个炮兵连曾在战争期间保卫过洛勃尼亚:纪念碑基座上有一架古老的高射炮,仿佛安装在铺着花岗石的巨大战壕里。战壕内壁上挂满了写着阵亡英雄姓名的牌子。街上有一个狭窄的入口通往那里,但无论从哪个方向都看不清战壕的内部。以前他经常和谢尔戈放学后在那里抽烟,而旁边的流浪汉喝着商标不明的伏特加。伊利亚和谢尔戈一边读着牌子上的姓名,一边寻找:谁找到的姓名更可笑,谁就赢了。流浪汉讲述与他们同在一个星球上的艰难生活。伊利亚记住了他们的话。然后他们去谢尔戈家里玩游戏机,趁谢尔戈的父母还没回来。之后他独自到街上走走,吹吹身上的烟味。如果妈妈闻到他身上的烟草味,那他就完蛋了。他从炮兵连大街跑过马路——这里已是仓库大街的起点。他的胸口开始隐隐作痛。这是一幢赫鲁晓夫式建筑:红褐色砖头,白色边框。歪斜的旋转木马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六层楼高的白桦树裸露着躯干。已经能看见自己的家了,伊利亚甚至找到了自家的窗户,而且是正对着的那扇。妈妈现在应该能看见他呀?她肯定跑来跑去地想看到他,同时加热饭菜。他向她挥了挥手。他走过车库。垃圾池上画满了各种“联盟动画电影”“联盟动画电影”是位于莫斯科的一家动画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36年6月10日。里的角色:小狮子、乌龟、小熊维尼指1969年苏联版《小熊维尼》中的主要角色。、小猪皮杰。它们早已褪色,现在正在蜕皮,笑眯眯的。车库上方绷着铁丝网,后面是铁路仓库区域,街道正是以此命名。一位老奶奶正在给垃圾池旁冻僵的鸽子弄面包屑,并靠提供的免费食物训练它们。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穿着长毛绒家居服跑出来扔垃圾。她注意到了伊利亚:看来有可能会在垃圾池旁相遇。她担心发生意外而掉转身子,然后提着垃圾袋顶着严寒迈着小碎步走向更远处的垃圾池。伊利亚只能将双手更深地插进口袋。到楼门口了。他对着门铃抬起手指。突然头晕目眩。按键还是那样,与七年前一样。门也一样。手指却完全不同了。门口里面是否依旧呢?还有屋子。还有妈妈。他按了:0-1-1。响了。叮咚叮咚。心儿也随之翻江倒海。他没想到自己会如此激动。有什么可激动的呢?这一天他想象了多少次啊。想象过这一天的多少啊。当不得不在号子里忍着——他想过这个门口,想过这个门铃,想过回家。有一些东西,不得不吞咽下去——只为了能回家,为了能重新成为正常人。怎样才能做到呢?去接着念完书。妈妈曾在电话里说:你不应该让他们毁了你。他们剥夺了你几年时光,但你还年轻。咱们能搞好一切。既然你能不靠贿赂就考进莫斯科大学,而且咱们是一起准备的,那么你就一定能回来。咱们不去语文系,也不去莫斯科大学,就去一般的学校。你有才华,聪明灵活,只求你不要让自己的智力僵化,不要让他们把你兽化。你有保护层。这个保护层能阻挡一切,阻挡所有的垃圾。不管你在监狱发生了什么,都不要往心里去。就假装这不是你。就好像这只是你必须要扮演的一个角色。而真正的你藏在衣服内袋里,悄悄地等待。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冒充英雄。你就照他们说的做。否则他们会毁了你,伊留沙伊留沙是伊利亚的爱称。。毁掉或干脆杀掉。不要企图战胜体制,但可以不引人注目,这样体制就会将你忘记。要等待,要忍耐。只要你回来,咱们就能搞好一切。邻居如果斜眼看你——咱们就去你向往的莫斯科。那里谁也不认识谁,那里的人记忆不超过一天。你还能为自己找个女友,就让她,让那个维拉走吧,我能理解她。只求你活着回来,只求你健康。如果你想画画,也可以,就去吧!二十七岁——一切才刚刚开始!门铃的那头无人接听。好吧,再来一次。0-1-1。也许,妈妈出去买食品了?酸奶或者面包可能没了。伊利亚慌慌张张地回头看了一眼:他没有钥匙。没有妈妈他进不去。他拽了一下结了冰的门把手。他往后退了几步。找到三楼自家的窗户。小气窗是打开的,像一个黑洞——在给厨房通风,而其他玻璃上映照出铅块一样的天空。天色渐黑。不是该开灯了吗?邻居家的灯已经亮了。“妈!妈……妈!”也许她就是出去了?他还要在这里站多久?或者应该去周边所有食品店看看?没面包——就算了呗!可以等他回来,他自己跑一趟。赶了两天的路,头发痒,肚子痛,而且从车站回家的路上,屎都到屁股眼了。“妈!妈……妈!!!你在家吗?!”窗户如铅般阴沉。突然有一种恐惧的感觉。0-1-2。“谁呀?”里面传来嘶哑的声音。谢天谢地。“伊拉大婶!是我!伊利亚!戈留诺夫!是的!妈妈不知为啥不开门!我回来啦!放我进去一下!已经服满啦!能开一下吗?”女邻居先在门孔处看了看。伊利亚特意站到灯下,好让伊拉大婶透过他这么多年累积的沧桑看清他本人。锁子咯吱响了一下。她走到平台上:穿着长裤,留着短发,脸庞浮肿,叼着女士香烟。她是一名仓库会计。“伊利亚。伊留什卡伊留什卡是伊利亚的爱称。。他们怎么把你整成这样了。”“我妈——您知道她在哪儿吗?打不通电话,现在……”伊拉大婶咔嚓一声点了一下打火机。又咔嚓一声点了一下。两颊深陷。她看了看楼层之间的垃圾管道——避开伊留沙的眼睛。“前天她……心脏突然不舒服。你抽烟吗?”“抽。可我打电话没人接……她被送到医院了,是吗?哪家医院?她带手机了吗?”伊拉大婶把一根细细的、带金箍的白色香烟递给他。“救护人员说——心肌梗死。大面积的。”她一口气噼里啪啦把一根香烟抽完。点燃第二根接着抽。“这……”伊利亚晃了晃头,感觉要窒息了,无法抽烟,“这是?……去急救吗?所以?”“他们当时给她……总之,尝试了。但路上走得太久。虽然是立刻出发了。”她沉默了。不想说出声,希望伊利亚自己领悟。“我们刚刚……我和她前天还说过话……我出来的时候……给她打了电话……她说……大概是午饭时候。”“嗯,是午饭时候。我五点左右去敲她的门……当时我要去肉店。想着也许可以给她带点什么。嗯……门没锁,她在地上坐着,穿着衣服。我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她不在了?伊拉大婶!”伊利亚靠着墙。“我对他们讲:你们为啥开得那么慢!”女邻居提高嗓音说,“什么时候呼叫的你们呀!而他们说——当时有另一处呼救,也很紧急,我们如何分身呢?接听的急救电话简直像磁暴,所有老人都昏迷不醒。不过我对他们说:老人与这有什么关系?你们应该感到羞愧!这个女人才六十岁!甚至不到六十!”“在哪里?送到哪儿了?”“就是咱们的市医院。你要去吗?是应该把她接回来。该想想葬礼的事了。这可是操心事,葬礼你可不懂,我刚安葬了自己的姐姐,你无法想象。这也要钱,那也要钱,到处都要钱!”“我去。但不是现在。我……之后去。”“是呀,你刚回来!要不,去我家吧?饿了吧?”“可我怎么进自己家?”“什么怎么……那里开着门。谁知道她把钥匙放到哪里了。去我家吗?”“不。”伊利亚转向自己家门。听了听里面有没有动静。伊拉大婶没打算回自己家,她很好奇。而伊利亚暂时无力抓起门把手。“我前天还和她说过话。”“是呀,这样的事经常有。刚刚人还在——突然就没了。她倒是经常抱怨心脏不好。但嘴里嚼一块药片,马上就好了。现在谁身体好呀?我自己也是——看起来没什么,但只要天气一变——头都要炸了。”“我过一会儿去。去救护中心……谢谢。”伊利亚推开门。走进屋里。打开过道处的灯。解开上衣,挂在钩子上。关上门。换上拖鞋。拖鞋已经准备好了。他站了一会儿。应该继续往里走。“妈妈?”他轻声说,“妈。”他一步跨进她的卧室。床是皱的,床垫滑了下来。相框里伊利亚的照片是倒着的,他仰面躺着。微笑着——自豪,快乐,脸上长满粉刺。他被语文系录取了。所有人都说——如果不送礼,是不会被录取的,但他国考考得那么好,没人敢不录取他。妈妈都准备好了。抽屉柜里的小匣子被抽了出来,就是她装钱的那个匣子。他往里瞅了瞅——钱没了。全被扒走了。他走进自己的房间。空荡荡的。妈妈不在这里了,伊利亚也就不在了。书架上的书不再是原来的顺序,科幻和经典混在一起,似乎有人在书里找过藏钱的地方。桌子上是他的旧画,以前用铅笔给卡夫卡画的插图,给《变形记》画的。铅笔在那儿放着。这是那晚之前他坐着画的,他被带走的那晚之前。七年来这一幅画还保持原样,而且所有的东西,除了书之外,全都原封不动,仿佛伊利亚只是在上大学一样。只剩下看一看厨房。如果厨房里没有,那就什么地方也不会有了。厨房很冷。窗帘被穿堂风吹得鼓起来。硬邦邦的白面包放在破损的彩色漆布上,旁边放着一把备用的小刀,风干的“爱好者”牌香肠还带着白油脂,皮上出现一环环的小圈。在了无生气的灶眼上——放着一口巨大的珐琅瓷平底锅。伊利亚掀开盖子。菜汤。满满一锅菜汤。他站在黑暗的厕所里。起初他无法解出便。之后流出一小股——他觉得,似乎在流血。不是通常睾丸缩回时流出的那种脓液,而是黑色的静脉血,稠稠的,脱了气。没有便后的轻松感。他望了望马桶——啥也没有。他用肥皂把手洗了两遍,然后用冰水洗了脸。像往常一样,他用长柄勺给自己盛了妈妈做好的菜汤,汤已经冷了,但他没有加热。他用刀子把变干的面包头弄碎,蘸了一点浓汤。他打开电视。电视上正在放映《喜剧俱乐部》《喜剧俱乐部》是俄罗斯一个幽默脱口秀节目,从2005年开始上映。。“什么密码?要不试试‘绍伊古’指当代俄罗斯政治人物谢尔盖·库茹盖托维奇·绍伊古,陆军大将,担任过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长、莫斯科州州长、俄罗斯国防部长,也是国际消防员和救援人员体育联合会主席。!”“哇!成功了!”“当然啦!绍伊古适用于任何地方!”整个大厅的人都龇牙咧嘴大笑。漂亮年轻的女人们在大笑。晒得黝黑但保养很好的男人们在大笑。伊利亚眨了眨眼。他什么也不明白。一个笑话也不明白。他把一勺冷汤倒进嘴里,塞进喉咙。又送了一勺,塞进喉咙。接着又是一口,两口,三口。为了妈妈。应该买伏特加。伏特加,这才是需要的东西。

“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2018-2019”请您来投票!《夫妻的房间 》[法]埃里克·莱因哈特 著

《活在你手机里的我 》[俄罗斯] 德米特里·格鲁霍夫斯基 著

《首都》 [奥地利]罗伯特•梅纳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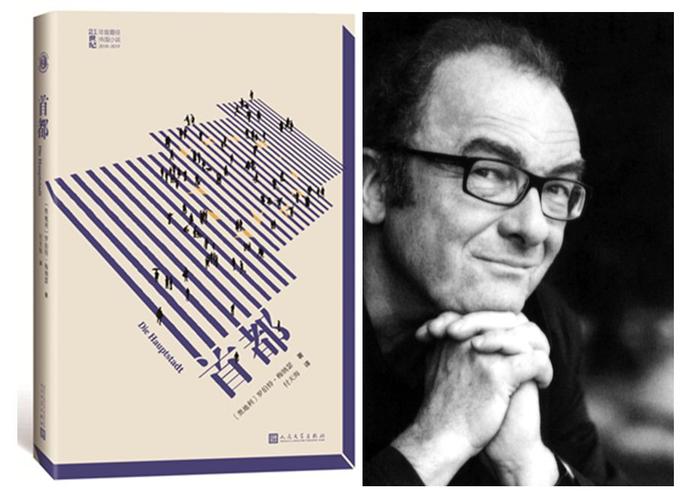
《已无人为我哭泣》[尼加拉瓜]塞尔希奥•拉米雷斯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