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做的非常简单,但也非常难,就是守护中文,用中文写出美丽的文章,让全世界去欣赏。
——严歌苓(2017哈佛中国论坛)
“尤其是身处异乡,说着异乡话,看着异国节目的我,让我写下去的动力就是把中国的文字,用小说这种载-体来写得好看,像《红楼梦》那么美。”
——严歌苓(第16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花儿与少年(选段一)
49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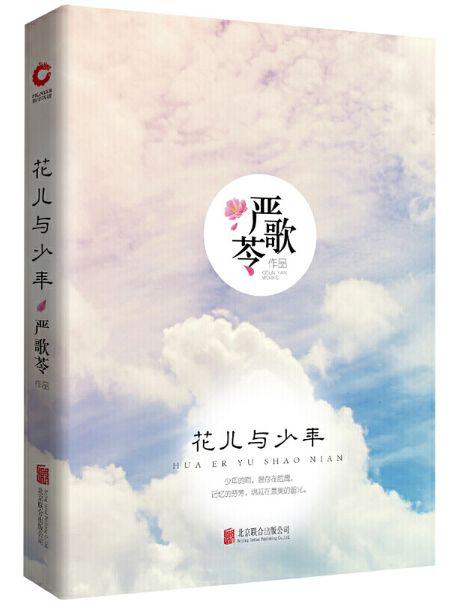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中篇小说集《花儿与少年》
......
徐晚江心想,死也得超过这个,省得他老回头对她挤眉弄眼。
这人至少一米九的个儿。二十五岁,或更年轻些。晚江断定他不比九华年长多少。她紧咬上去,与他之间仅差五米。不久,四米,三米。她已超过了一个四十岁的红发男人和一对女同性恋。海水正蓝,所有长跑者都被晚江杀下去。只耗剩了“一九O”。
她的两条腿非常优秀。谁若有稍好的眼力,会马上识破:这是两条被从小毁了又被重塑的芭蕾舞腿。
“一九O”又一次回头。他向晚江眨动一下左眼,飞快一笑。他的五官猛一走样。晚江知道,她自己的面容是也忽丑忽美。每个长跑者的面孔都是瞬间这样,瞬间那样,飘忽无定。
只差两米了。晚江拿出当年上弹板助跑的速度。“一九O”听着她柔韧的足掌起、落,起、落。他认为不妨再给一个勾引的微笑。谁让她找死?她这样死追他,不就是猎物追猎手吗?不如再进一步逗逗她。他让她超了过去。
现在是猎人追兔子了。晚江想,这下你别想再往我胸脯上看,变相吃我豆腐。
“一九O”总算领教了晚江的实力。他动真格的了,撒开蹄子狂奔,打着响鼻,碗口粗的喘息吹在晚江后脑勺上。晚江绝不能让他追上来,跟她并肩前进。那样瀚夫瑞会误会他年轻的妻子和“一九O”的金发青年勾搭上了。
前方是那个古炮台。转过弯后,就彻底安全了。瀚夫瑞即便用望远镜,也休想继续盯梢。晚江只能用长跑甩掉瀚夫瑞。否则他可以全职看守她,他把它看成两情相守。十年前,他把晚江娶过太平洋,娶进他那所大屋,他与她便从此形影不离。他在迎娶她之前办妥退休手续,就为了一步不离地与她厮守。晚江年少他三十岁,有时她半夜让台灯的光亮弄醒,见老瀚夫瑞正多愁善感地端详她。如同不时点数钞票的守财奴,他得一再证实自己的幸运。
此后,瀚夫瑞果真说话算话:跟着晚江上成人学校,她学英文,他修西班牙文、修音乐史、美术欣赏、瑜伽,有什么他修什么,只要他能和晚江同进同出。他一生恶狠狠工作,恶狠狠投资存钱,同时将大把时间储下,多少钟点,多少分秒花销在晚江身上,都花得起。何况他认为晚江疑点颇大,甚至有“前.科”。“前.科”发生在进成人学校第二周,晚江班上的老师临时有急事,晚江就给同班的墨西哥小伙子约到咖啡室去了。等瀚夫瑞心如火焚地找着她时,那墨西哥小老乡着迷地盯着晚江跟瀚夫瑞打招呼:“您的女儿真美丽。”往后瀚夫瑞更不敢大意。直到晚江的女儿仁仁开始上学那年,晚江对瀚夫瑞说:“明天早上我要开始长跑了。”瀚夫瑞说:“长跑好啊,是好习惯。”第一个早晨晚江就明白,瀚夫瑞根本不是对手。在三四百米光景,他还凑和跟得上她;到了五百米,他惨了,眼睛散了神,嘴唇垂危地张开。他深信自己会猝然死去,并在晚江眼里看到同样的恐惧。那以后,他就在四百米左右慢下来,眼巴巴看晚江矫健地撒腿远去。
那以后,晚江就这样沿着海湾跑,投奔她半小时的自由独立。
废弃的炮.台出现了。晚江开始减速,为全面停止做准备。对身体的把握和调控,晚江太是行家了。十岁开始舞蹈训练的晚江,玩四肢玩身板玩大的。“一九O”大踏步超过去,人渐渐没了,脚步声却还在炮.台古老的回音里。不一会儿,红发男人也赶上来。晚江想,他们你追我赶往死里跑图什么?他们又不缺自由。
女同性恋两口子也赶上来了。
晚江进一步放慢速度。他们这么鬼撵似的跑,又没人等在前头。而晚江是有人等的。很快,她看见九华的小卡车停在一棵大柏树下。晚江和九华从不事先约定。九华若时间宽裕,便在这儿停一停,等等她。他上班在金门桥那一头,晚江跑步的终点恰在他上班路线上。九华若等不及,走了,她也会独自在这里耽误三十分钟,从瀚夫瑞的关爱中偷个空,透口气。
九华见她过来,摇下车窗。她一边笑一边喘气。九华赶紧把一块旧浴巾铺到绽了口子的座位上。
“一九O”此刻折了回来,水淋淋地冲着晚江飞了个眼风。但他马上看到了九华。心顿时凉了下去。他心凉地看着九华为她拉开锈斑斑的车门,她钻了进去。在他看,这个漂亮的亚洲女人钻进了一堆移动废铁。他把九华当成她相好了。
九华摘下保温瓶上的塑料盖,把滚烫的豆浆倒进去,递给晚江。九华住在.新TANG REN JIE(严歌苓读书会注:此处原文并非拼音。请大家自行转换),那儿不少糕饼店卖鲜豆浆。晚江问他昨晚是不是又看电视连续剧了。他笑着说:“没看。”晚江说:“哼,没少看。”
九华说:“就看了四集。”
“就看了四集?。实在有工夫,读点书啊。你一辈子开卡车送饭盒?”
九华不接茬了。他每次都这样,让她的话落定在那里。九华是没有办法的,他不是读书的命。
晚江也明白,她说这些是白说。每回话说到此处,两人便有点僵。一会儿,她开始打圆场,问他早晨忘没忘吃维生素。又问他跟他爸通了电话没有。九华就是点头。一点头,头上又厚又长的头发便甩动起来,便提醒了晚江,这是个缺乏照应的孩子;二十岁是没错的,但一看就是从家里出逃,长荒野了的男孩。
晚江从裤腰里摸出几张减价券。洗衣粉一盒减两块钱,比萨饼减一块,火腿减三块。九华接过去,在手里折来折去地玩。晚江慢慢喝着烫嘴的豆浆,不时从远处收回目光,看他一眼。九华比六年前壮实多了,那种苦力形的身板。他很像他爸,却还不如他爸俊气。她一再纳闷,仁仁跟九华怎么可能是兄妹。
六年前,瀚夫瑞和晚江把九华从机场接回来,路易正张罗着挪家具,为九华搭床铺。他以那永远的热情有余、诚恳不足的笑容向九华伸出手:“Welcome,How are you?”
九华信中说他一直在念英文补习班,此刻嘴里却没一个英文字儿。
瀚夫瑞见两个将要做兄弟的陌生人开头就冷了场,便慈父般的低声对九华说:“别人说‘How are you’时候,你该说:‘Fine,How are you?’或者:‘Very well.Thank you.’记住了?”
九华用力点头,连伸出去给路易握的手都憋成了深红色。他在自己卧室闷坐一会儿,不声不响到厨房里。晚江在忙晚饭,他替她剥蒜皮,削生姜,洗她不时扔在水池里的锅碗瓢盆。晚江不时小声催促:“往那边站点儿……快,我等这锅用呢。”他便闷头闷脑地东躲西让,手脚快当起来,却处处碰出声响。晚江冷不丁说一句:“把Soysauce递给我。”他不懂,却也不问,就那样站着。晚江怜惜地撸他一把脑袋,挤开他,悄声笑道:“哎呀闷葫芦。记着:酱油叫Soysauce。”她把酱油瓶从吊柜里够下来。他眼睛飞快,偷瞟一眼酱油瓶,用力点点头。
“发一次音我听听。Soysauce──”
他抿嘴一笑。晚江歪着头看着这半大小子,微笑起来:“不难嘛。你不肯开口,学多少年英文还是哑巴。”她目光向客厅一甩,嗓音压得极低,“人家路易,讲三国语言……”但她马上意识到这样对比不公正,挤对九华。她把手掌搭在他脖梗上,动作语气都是委婉慈爱:“咱们将来也上好大学,咱们可不能让人家给比下去。咱们玩命也得把英文学好喽。”
九华点了几下头,缓慢而沉痛,要决一死战了。他十四岁的体格在国内蛮标准,一到这里,显得又瘦又小,两个尖尖的肩头耸起,脚上的黑棉袜是瀚夫瑞打算捐给“救世军”的。袜头比九华脚要长出一截,看去少去了一截足趾。晚江又说:“盐叫Salt,Salt。”
他以两个残畸的脚立在豪华的大理石地面上,无地自容地对母亲一笑。
“你看妈三十八岁了,还在每天背新单词。”晚江指指冰箱上的小黑板,上面记着几个词汇。“你学了几年,一个词也不肯说,那哪儿行啊……”
他点着头,忽见晚江又把一个锅扔进水池,得救一般扑上去洗。
晚江看着儿子的背景。他在这一刹那显得愚笨而顽固。
那天的晚餐成了席:六个冷盘,六个热菜,路易摆了花卉、蜡烛。连一年不露几面的苏,也从地下室出来了。穿着晚江送她的裙子,好好梳了头。仁仁这年八岁,说起外交辞令来嘴巧得要命。她最后一个入席,伸手同每个人去握,最后接见她的亲哥哥:“欢迎你来美国。”瀚夫瑞看着仁仁,洋洋得意。仁仁又说:“欢迎你来家里。”她的气度很大,家也好美国也好,都是她的。
路易此时站起身,举起葡萄酒,说:“欢迎你──”他自己也知道他的中文可怕,改口说英文:“旧金山欢迎你。”
九华愣怔着,听晚江小声催促,他慌忙站起,高脚杯盛着白开水,给悬危地举着,像他一样受罪。
“我们全家都欢迎你。”路易进一步热情,进一步缺乏诚恳。他把杯子在九华杯沿上磕一下。
“旅途怎么样?”他坐下去。
“……”九华赶快也坐下去。
“还好吧?”
“嗯。”
晚江只盼路易就此饶了九华。却在这当口,瀚夫瑞开了口:“九华,别人说‘欢迎’的时候,你必须说‘谢谢’。”
九华点点头。
“来一遍。”瀚夫瑞说,手指抬起,拿根指挥棒似的。
九华垂着眼皮,脸、耳朵、手全是红的;由红变成暗红。整个餐桌上的人什么也不做,一声也不出,全等九华好歹给瀚夫瑞一个面子,说个把字眼,大家的心跳、呼吸得以恢复。
“Sank you。”九华说:“不是Sank you,是Thank you。”瀚夫瑞把舌头咬在上下两排假牙之间,亮给九华看:“Th──ank──You.”
“Dank you。”九华说。
“唔──”瀚夫瑞摇着头,“还是不对。也不是Dank you,是Than kyou。要紧的是舌头……Th──anks,Th……明白了吧?再试试。”
“……”九华暗红地坐在那里,任杀任剐,死不吭声了。
仁仁这时说:“快饿死啦。”
她这一喊,一场对九华的大刑,总算暂时停住。路易开始说天气。他说每年回来过寒暑假真是开洋荤,西部的气候真他妈棒,而他上学的明尼苏达,简直是西伯利亚流放地。
这时苏把一盘芹菜拌干丝传到晚江手里。晚江夹了一点,递给九华。九华迅速摇摇头,人往后一缩。晚江小声说:“接着呀。”他还摇头,人缩得更紧。她只得越过他,把盘子传给仁仁。
仁仁接过盘子,说:“我不要。”她将盘子传给瀚夫瑞。
“不要,应该说:‘不要了,谢谢。’”瀚夫瑞往自己盘子里夹了一些菜。
瀚夫瑞和颜悦色,对仁仁偏着面孔。他跟童年的仁仁说话就这样,带点逗耍,十分温存。他说:“怎样啦仁仁,‘不要了’,后面呢?”
人们觉得他对仁仁好是没说的,但他的表情姿态──就如此刻,总有点不对劲。或许只有苏想到,瀚夫瑞此刻的温存是对宠物的温存,对于一只狗或两只鸟的温存和耐心。
“噢,不要了,谢谢。”仁仁说。瀚夫瑞这样纠正她,她完全无所谓,毫不觉得瀚夫瑞当众给她难堪。她说:“劳驾把那个盘子递过来给我。”她似乎把这套斯文八股做得更繁文缛节:“Many Tanksin-deed。”莎士比亚人物似的,戏腔戏调。你不知她是正经的,还是在耍嘴皮。
瀚夫瑞说:“九华,菜可以不要,但要接过盘子,往下传,而且一定要说:‘不了,谢谢。’”
九华堵了一嘴食物,难以下咽,眼睛只瞪着一尺远的桌面,同时点点头。
“你来一遍:“No Thanks。”瀚夫瑞说。此刻恰有一盘鲜姜丝炒鱿鱼丝,传到了跟前,九华赶紧伸手去接,屁股也略从椅子上掀起。他太急切想把动作做出点模样,胳膊碰翻了盛白水的高脚杯。
晚江马上救灾,把自己的餐巾铺到水渍上。她小声说:“没事没事。”
这一来,上下文断了。九华把接上去的台词和动作忘得干乾净净。
瀚夫瑞说:“说呀,No,thank you。”他两条眉毛各有几根极长的,此刻乍了起来,微微打颤。
九华一声不吱,赶紧把盘子塞给晚江。
瀚夫瑞看着九华,嫌恶出来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无望的人:既笨又自尊。
整个餐桌只有苏在自斟自饮,闷吃闷喝。她很少参加这个家庭的晚餐,但剩在冰箱里的菜从来剩不住,夜里就给她端到地下室下酒去了。人们大致知道她是个文文静静的酒徒,只是酗酒风度良好,酒后也不招谁不惹谁。她本来就是个省事的人,酗酒只让她更加省事。几杯酒下去,她自己的空间便在这一桌人中建筑起来,无形却坚固的隔离把她囿于其内,瀚夫瑞和九华的冲突,以及全桌人的不安都毫不打搅她。她在自己的空间里吃得很好,也喝得很好。眼圈和鼻头通红通红,却有个自得其乐的浅笑,始终挂在脸上。
“怎么了,九华?”瀚夫瑞心想,跟一只狗口干舌燥说那么多话,它也不会这样无动于衷。
晚江注意到九华一点儿菜都没吃。传到他手里的盘子,他接过便往下传,像是义务劳动,在建筑工地上传砖头。她赶紧舀一勺板栗烧小母鸡:“小时候你最爱吃这个。”
九华皱起眉,迅速摇摇头。
瀚夫瑞看一眼晚江。他的意思似乎是:你有把握他是你儿子?不会是从机场误接一个人回来吧?难道这个来路不清的半大小子从此就混进我家里,从此跟我作对?你看他的样子──眉毛垮着,连额前的头发都跟着垮下来;他怎么会有这样一头不驯顺的头发?这样厚,够三个脑袋去分摊。
其间是路易挨个跟每个人开扯:说晚江烧的菜可以编一本著名菜谱。又跟仁仁逗两句嘴,关于她小臂上的伪仿刺青。他说伪仿文身真好;假如你三天后变了心,去暗恋另一个男同学,再仿一个罢了,不必给皮肉另一翻苦头吃。路易就这点好,总是为人们打圆场,讨了无趣也不在乎。
“苏,巴比好吗?”路易问苏。
巴比是苏的鹦鹉。苏说巴比两年前就死了,不过多谢关心。巴比的继任叫卡美哈米亚(卡美哈米亚(Kamehamea)夏威夷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王。)。路易说他为巴比的死志哀。苏说她替在天有灵的巴比谢谢路易,两年了还有个记着它的人。路易又问:卡美哈米亚怎么样?精彩吗?苏说:卡美哈米亚比较固执,疑心很重,要等它对她的疑心彻底消除了,才能正式对它进行教育。同父异母的姐弟看上去很谈得来。
那顿晚饭是靠路易见风使舵的闲聊完成的。当晚九华早早撤进他的卧室。晚江悄悄对路易说:“谢谢了。”她给了他一个有苦难言的眼风。路易把它完全接住,也来一个死党式的微笑,悄声说:“免啦──我份内的事。”
她看着他年轻的笑容。他又说:“这个家全靠我瞎搭讪过活。”
晚江在路易瞬间的真诚面前不知所措了。她大惊失色地转身就走。路易看着她上楼,逃命一般。他想她惊吓什么呢?他和她之间隔着一万种不可能,太安全了。
此刻的晚江坐在九华旁边,喝着凉下去的豆浆。九华不断给她添些热的进来。
“你见你爸了吧?”她问。
“嗯。”
“他烟抽得还是很厉害?”
“嗯。”
“叫他少抽一点。”
九华点点头。
“说我说的:美国每年有四十万人员是抽烟抽死的。”晚江说着把暖壶盖子盖回去,表示她喝饱了。
“他不听我的。”九华笑一下。
“让你告诉他,是我说的。”晚江说。她不知道自己神色是娇嗔的,是年轻母亲和成了年的儿子使性子的神色。
“行。”九华说着,又一笑。
“让他少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管什么用啊?我又不在那儿分分钟享福。”
“妈,不早了。”
“没事看看书,听见没有?不然以后就跟你爸似的。”她推开车门,蜷了身钻出去。
然后她站在那儿,看九华的卡车开下坡去。她一直站到卡车开没了,才觉出海风很冷。回程她跑得疲疲沓沓,动力全没了。六年前那个“欢迎”晚餐之后,九华开始了隐居。他每天早晨很早出门,搭公车到学校去。晚饭他单吃。晚江其实给他午餐盒里装的饭菜足够他吃两顿。晚饭时间一过,他会准时出现在厨房里,冲洗所有碗碟,把它们放进洗碗机。如果瀚夫瑞或路易在此地碰见他,他便拼命佝着身,埋头摆弄洗碗机里的餐具。偶然地,瀚夫瑞会问他为什么不同大家一块儿吃晚饭。晚江便打马虎眼,说他功课压力大,在学校随便吃过了。晚江一边替九华开脱,一边盼着九华能早日在这个家庭里取得像苏那样的特殊待遇:没任何人惦记、怀念、盘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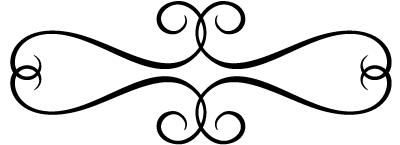


中篇小说《花儿与少年》
2005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排行榜榜首
多年前,年轻的女主人公徐晚江和丈夫同为军区舞蹈演员,纵然贫苦却浪漫安然。为了让一家人过上充裕的生活,两人商量离了婚,她嫁给了一个偶然结识的、富足的美国人。十多年来,她不动声色地挣钱,助力将前夫和孩子都移民到美国,并且开始想象新的未来……而现实却正在悄悄地变得满目疮痍......
严歌苓曾创作过大量移民背景的小说,《花儿与少年》便是其中一部中篇代表作。小说成书出版于2004年,由昆仑出版社以“长篇体量”出版发行。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为小说作序,并被其誉为“二十一世纪版的《雷雨》”。

我很少以这样客观的角度去写一部小说。那种带人渐入其境、向人娓娓道来的写法对于我来说实在太烦闷。长篇小说的创作者假如感到始终烦闷,那就太自找苦头了。因此我一旦要写几万字的小说,就想给自已找了解网的形式。所以我的长篇小说都很实验,短篇小说都很传统。形式变了,劳动过程就不单调了。我能老老实实呆在《花儿与少年》的故事之外,沒有给自已上台的机会,把这篇小说写下来,对于我是个考验。自从我主动给国内投稿之后发现国内读者们对传统叙事方式接交得好一些,坦白说:这篇小说是我争取他们接交的一个姿态。我选它,因为它是我写实功力表现得比较全面的一篇作品。
——2006年《严歌苓自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