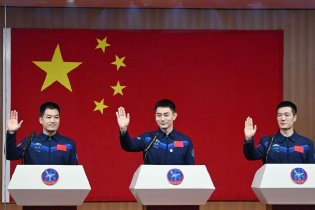艺术

1979年4月,“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在中山公园举办,轰动了当时的北京社会,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变革中“春天”的重要标志。2019年4月,“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迎来四十周年之际,“四月影会40周年纪念展”在北京798艺术园区举办,展出当年参展摄影作品及珍贵文字资料,复原“四月影会”第一回展基本样貌。《今天》123期“艺术”专栏,收录两场展览相关照片及文章,和读者一起拼贴“两个四月”的影像记忆。
点击阅读:鲍昆《返回历史现场的意义》、闻丹青《策展心绪》,“自然·社会·人 第一回展”作品精选
历史匆匆地走到了今天。如果从一九七六年那结束十亿中国人十年噩梦的一刻算起,刚好又是一个十年。人们称这十年为所谓的“新时期”。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但它对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十年。这十年值得回味的事情太多了,作为生活风帆的文学艺术,一直处于新时期的航道前沿,为中国经济的振兴,中国文化的复兴,充当着领航员的角色。
摄影,这一新鲜的艺术样式和传播媒介,在新时期中获得了比任何其它艺术样式都更为壮观的发展。自然,它也和其它艺术一样,被历史蹒跚的脚步踩上了深深的印记。
和其它艺术一样,摄影这本来是有钱人附庸风雅的技艺,从一九四九年起,充当了翻身的革命中国人改天换地的政治号角。那是一个红色的年代,一切其它的色彩都黯然失色。战争的胜利、新生活给予人们政治上的平等和物质分配上的平均和拮据,鼓舞着整个社会开创新世纪的疯狂激情。人们对旧社会的一切视为污泥浊水,欲彻底荡平而后快。花前月下怎能成为志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战士应有的情怀?照相机应是歌颂报道祖国大好形势、反映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不单是由战争年代走来的摄影记者的认识,也是整个社会对照相机的要求。于是,革命的摄影记者以革命的情感摄影,革命的群众也以革命的要求认同摄影,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摄影特征。同时,生活的贫困也限制着大多数人们拿起照相机。挎相机的人是多么的荣幸和骄傲,甚至比背枪者还光荣!另外,对于革命苏联老大哥弟弟式的崇拜,也使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摄影家们打上了苏式的印记。俄罗斯以赞颂崇高为基调的美学规范在中国找到了它最理想的摹本。没有活泼的对自然世界的光和影的新鲜感受,没有对人的命运的深刻理解,高昂的塔吊下是庄严朴素的建设者,钢铁工人的肖像比米开朗基罗手下的大卫还要庄严,这是一代摄影家的追求。如果说,那时人们认为口号等于艺术的话,摄影的等式则是新闻等于艺术。我们没有必要责难那个时代以及那些人们,那是历史给我们民族开的玩笑。集体的追求,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积淀的道德理想弘扬,是那个时代我们民族所认同的风尚。
进入六十年代中期,我们把本来还显质朴的激情推向了极端,一切都开始走向反面。文学艺术已无自身的本质特征规律而言,个性的光彩被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抹杀,审美的理想被专政的铁拳砸得荡然无存。摄影自然更逃不出这场劫难。本来就浅薄不成熟的这一艺术样式,更为一小撮昧良心的政治骗子当成夺取权力和毒化异化人们心灵的下流政治工具。林副统帅学毛选的虚伪镜头为多少善良的人们顶礼膜拜,政治家们精巧的“换头术”不是曾改变了历史前进的速度。摄影没有以自己纪实性的特长记录这一切,却是以自己可悲的命运为这一难堪的时刻做了历史的鉴证。
物极必反。人们往往是无私地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奉献出去之后,才会感到它的珍贵。同样,当人们用自己的血肉砌起了却一座神像之后,才感到这神像是多么的虚无。迷狂之后就是粉碎,四·五运动终于在积愤已久之后爆发!这场伟大的运动的特点之一就是人们用照相机做武器,愤怒地表达了沉郁内心许久的对人的尊严的渴望。与其说当时的人们是为了敬爱的周总理鸣不平,不如说人们是为人性的泯灭和自身悲惨的命运愤怒抗议。摄影就在这个伟大的时刻第一次真正地走进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摄影在这次大普及中的姿态是奇特的。它不是艺术的,而是政治的;它不是沙龙的,而是群众性的。或许当时许多人对照相根本就不怎么懂,但那又有什么,举起相机本身就是一次充满激情的愉悦,是一次真诚的自我表达和自我人格的证明。中国人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自我的存在了,感谢照相机给了人们压抑在躯体深层的生命激情一次宣泄的契机。这是世界摄影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达盖尔在天之灵若有幸感知这一切的话,当会无比欣慰。
四·五运动使中国人学会了在人生中使用照相机,懂得了摄影的生命意义,它是中国摄影普及的发端。同时,它也造就了一代摄影家。在天安门广场乌云般的人群中,走出了一批年轻人,四·五运动点燃的星星之火被他们高擎在手中,燃成了熊熊烈焰,这是一次深刻的历史性的转折。这其中孕含的文化上的意义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这批年轻人为中国摄影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永远值得人们纪念的努力。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批参加过四·五运动的年轻人聚合起来自发举办了轰动社会各界的“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并结社成为“四月影会”。这是新中国诞生以来的第一个民间摄影团体和第一个民间摄影展览。照相机在中国从此获得了姿态上的大转折,它的神圣化和特权被打破了,具有了更为广泛的价值意义。无数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把照相机从生活留影的狭窄天地解放出来,用它参与生活,进行艺术创造,用它作为第二自我的生命再现。不能不承认,从四·五发端的摄影运动到四月影会的第一回影展,在中国摄影史上所具有的革命的意义。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这种新形式所具有的真正特有的美学价值,第一次广泛、充分的在中国人民大众之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展览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短短的二十天里,接待了近七万人众,狭小的中山公园兰室展厅(150平米)内摩肩接踵,展览一时成了北京市民时髦的话题,这情景极像一九五五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天下一家”影展时的情景。
“自然·社会·人”展览的三百余幅作品,在今天看来,或许是十分幼稚的。如果从工艺角度去要求,甚至可以说是一堆废品,有些作品连适当的修整都没有,作品大大小小,没有统一的格调,严肃与抒情、粗犷与细腻别别扭扭地拥挤在一起,甚至一些生活留影也滥竽充数夹在中间。在这些作品中,凡人的真实情感,都不加修饰地、活泼地、和因为迫不及待而显得粗糙地袒露在画面上。三百多幅作品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大自然惊人奇丽的一瞬、普通人言谈行止时真切感人的刹那、富于哲理和思考的小品……全都无私而真诚地捧给了观众。生活,在这里既沉重又轻松,既肃穆又诙谐,一切来得那么坦坦荡荡,落落大方。在这种亲近的气氛中,人们发现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原感单调、平凡的生活,居然竟那么有声有色,生活竟然还有那么多的美好。这一切,怎能不使刚从红海洋淋浴出来的人们心驰神往?况且,当人们看到一些早被一代人“理智”所遗忘的人本的存在被照相机重新再现出来时,惊诧之余又会是多么激动,那原本是他的生命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呀。如李晓斌的《……好吗?》,一对恋人在泼洒着春光的草地上心心相印,令人不禁感叹美妙的青春;而王苗的《冷与热》则把火热的青春之恋放进了严寒,在生动的对比中把我们引进那蹂躏人之尊严的艰难岁月;金伯宏的《| 5︵1 23| 4- |》和《悠闲》用诙谐、苦涩的微笑,讲了两个古老而又现实的中国故事。值得称道的是,一部分作品有着较强的幽默意识,观后令人忍俊不住之余又领悟到某种哲理。这种效果,除了作品形象本身的生动外,显然与一部分作品文学性的标题和配诗有关。有些诗以平铺直叙的白话方式,读来却十分精彩。如李江树的《画家石鲁》的配诗:“总算活过来了/ 黑的画家 / 白了一头青丝 / 掉了一口白牙”在这些最明了、最简单不过的寥寥几语中,隐含着最曲折、最深切的悲愤。

李晓斌《……好吗?》

王苗《冷与热》

金伯宏《| 5︵1 23| 4- |》

李江树《画家石鲁》
然而就是这些粗劣的作品,才第一次给新中国的摄影注入了人的气息,中国的摄影到底可以堂而皇之地称作“艺术”了。这可以从无数洋溢着热情的观众留言中找到证明:
“从这个绝美的影展,我闻到了新的气息,这是时代的气息。”
“你们给中国摄影艺术的身躯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我第一次感到了摄影艺术离我这么近,这么亲切!”
是什么使善良的北京人如此激动地认同这个展览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摄影艺术新的理解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自然·社会·人”影展所给予人们社会学意义和艺术价值取向的启示与思考。
“自然·社会·人”影展诞生在春光明媚的四月。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恰好是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思想解放运动正磅礴兴起,十亿中国人长久压抑的创造激情像敞开闸门的高坝之水,喷涌而出。文学上首开先河的一批作品相继问世,如《班主任》、《伤痕》等。文学首先向披着左倾马克思主义实则封建专制的非人性文化鸣枪了。这批作品肤浅、幼稚,但却勇敢地使其自身取向贴进文学原来的本体特征,人类原有的伤感、迷离、希冀、温情和欢乐又开始回到了作家的笔下。紧接着,思想界提出了“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出发点”这一主张,力求在理论上为新时期文化复兴推波助澜。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一观点可能有些地方失之科学上的严密,但在当时乍暖还寒时节,是多么令人振奋,它到底道出了无数中国人渴求自我尊严的心声。
这股呼唤人性复归的劲风,几乎刮遍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自然·社会·人”相继出现的“星星画展”是在美术领域内的爆炸新闻。也是一群被文化革命摧残蹂躏的青年画家,在街头挂起了一批“七歪八扭,离经叛道”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中的形象已很少有通常为人们所熟悉的优美、和谐的古典美学特征,而带有当时中国人还十分鲜见的主观自我表现色彩。许多形象是扭曲、变形和荒诞的,明显地暗喻一代人对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辛酸陈述和对生活前途渺茫的探索、希冀。作品中凝聚的思想情感是复杂混乱的,一切再也不是那么单纯。这批当时未名的画家们,除了给历史和现实划了一个问号外,还头一次撞开了对外封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文化之门,自觉地使自己的作品融进了二十世纪的世界艺术观念。这实在是石破惊天之举。
“自然·社会·人”正是在这个伟大的觉醒之刻诞生的,甚至可以说它是这一时刻的敲钟者之一。中国摄影在一九七九年是自豪的,因为它是与时代同步的。人们在四月的影展上看到的绝不仅是逼近生活的可亲可感的图像,更让他们激动的是整个影展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和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曙光。
在我们肯定这届被后来人们称为“自然·社会·人”第一回展之余,我们似也应看到它与“星星美展”以及其它一些民间文学刊物之间存在的距离。它缺少对社会、人生深刻而理性的沉思,缺乏对于特定时代人的命运的悲剧性揭示,显得有些浅薄而致使大有份量不足的遗憾。与美术相比,摄影的现实之所以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来的摄影队伍素质的差异。当然囿于中国独特的社会条件,这一切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于健鹰《窗》

贾育平《搏》
由于第一回展的成功,四月影会在一九八零年又兴致勃勃地举办了第二届“自然·社会·人”展览。由于第一回展览的影响,这届展览参展的作品和作者规模都大多了。和第一回相比较,当初冲脱时的激情渲泄开始显示出了转入思考的痕迹,技术上的进步十分明显。虽然整体上没有长足的进步,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一些很有特点的作品,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如李英杰的《稻子和稗子》、凌飞的《只有思想在流动》、任曙林的《三儿说下午去钓鱼》、孙青青的《苇塘深处》和吕小中的《河神的套鞋》等。这些作品都各以特长取得了某些方面的成功。然而在这届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李京红的《救救孩子》。这幅作品展出后,引起了一场喋喋不休的关于抓拍与摆拍的论战。本文没有兴趣讨论争论的是与非,实际上应该探讨的是,作者在这幅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参与意识。摄影就表现媒介的品格来说,优于其它艺术样式。它真切的形象、快速的再现(既使中间含有虚伪)颇能获取一般人的信任,因此,它在人类现代生活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从摄影文化的高度看,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拍摄是摄影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好比报告文学在文学中的地位一样。李京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那个时候,就积极地参与了生活,明确地去揭示生活中值得引起人们注视的社会问题。
“自然·社会·人”除了它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外,在艺术上也是独具价值的。从文艺学的角度上说,它是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较典型的现实主义展览,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个按艺术规律来展示摄影魅力的展览。它以整体的面貌开创了摄影艺术的真实,这在被“重大题材论”、“艺术为政治服务”、“新闻摄影就等于艺术”等观念模式禁锢二十多年的时代里,是多么不容易的起步,又是多么珍贵的起步啊!这批年青人用小人物的内心体验创造了充满人的情感的世界、痛苦、欢乐、困惑、期望、思索……
一九八一年,“自然·社会·人”的组织者们又举办了第三回展。这次是在“中国的卢浮宫”——中国美术馆揭幕的,堂而皇之。场地的升迁,折射出历史的变迁。一九八二年的中国已开始扬起了改革的大旗。文学的脚步继续稳健地迈进。主题的深化,题材的拓展以及“意识流”小说被中国大众的终于接受,都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强劲势头。美术界“星星美展”的第二次展览,锋芒毕现,它“极端”的艺术观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捍卫者们对它的坚决而有力的敌视和制裁。“自然·社会·人”值此复杂时刻,推出了自己的作品,在当时也是相当令人瞩目的。或许是中国美术馆的殿堂过分高雅,展览也平添了几分沙龙气,结果反而使本来充满希望的观众有些扫兴。不过的确这些作品有着较强的沙龙倾向,显示了几年来一批作者在艺术上的成熟。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无论从制作到意象,都显示出一定的流派风格意识和唯美的倾向。令人遗憾的是,它明显缺少一、二届展那种质朴亲切的特点,刻意精致下透着一股沙龙情调的冷漠,而且也缺少对血肉生活的敏感和激情。
尽管这样,第三回展还是相当成功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几位曾在前两回展览中已初露个人风格的端倪的作者,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风格意向,有意识地对现代艺术风范进行了探索赏试。如展览的主要组办者之一王志平的作品,李晓斌的作品。以及王苗、罗小韵的作品。
王志平的《女画家肖像》是采用类似美国波普艺术大家劳生柏的“结合艺术”手法制作的。这种所谓的“结合艺术”就是把一些质量完全不同的材料通过拼贴和粘结,以求得一种内在精神上的和谐统一。《女画家肖像》即是照片拼贴和绘画相结合而成的。如果我们对照劳生柏的大量作品,王志平无论从手法和意象上都显得十分幼稚,但这毕竟是中国摄影家第一次表现出来的超越摄影模式的尝试和对二十世纪人类文化艺术的一种接纳态度。这是难能可贵的。王志平一直是一个充满创造欲望的摄影家,他在这次展览中的其它作品和后来的一系列作品,都体现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倾向。
王苗,罗小韵的风光小品,在这次展览中也颇为引人注目。她们对光,色调等摄影语言的运用很为精致考究,极其投合一般欣赏者的口味,以后果然这种格调的作品在中国摄影界蔚为大观。

张炬《雪里送炭》

忻迎一《根》
第三回展览尤其值得令人回味的是另外两个人的作品,这就是李晓斌和张艺谋的作品。
李晓斌推出了一组纯客观的作品,这是一组高度现实主义的没有任何雕琢的街头影像。为人们习惯接受的典型、崇高、优美、和谐的艺术法则,李晓斌都一股脑儿地抛弃了。这与整个第三回展弥漫的那种崇尚形式感和技巧化的气氛形成截然分明的黑白反差。李晓斌似乎还不满足于这些照相似的作品对整个展览造成的不和谐,又在作品上写下了如下宣言:
“我认为:内容本身就是形式。就作品本身而言,内容形式同样重要。我力求用摄影独有的特点,去表现生活中美的或不一定美但却真实自然的——我却以为是美的。这组照片就是力求对摄影艺术语言作一些探索。在生活中,抓拍的这组人物,我不想加以任何褒贬。因为我并不认识和了解他们,只想通过照片中的形象,给人以感受。
不写题目是因为不同的观众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况且往往比作者更高明些。”
李晓斌的这段宣言和那组作品在当时都是令观众以及他的艺术伙伴们讨厌的。他们无法认同这样的摄影,甚至认为这是亵渎和荒谬。因为一切离神圣的艺术祭坛太遥远了。这组不受欢迎的作品在这届展览中成为最受白眼的,显得可怜巴巴。它的出现使作者本人也一时成了人们愤怒和讥讽的话题。
这是六年前的事情了。当时间洗去了历史不同时期绚丽的彩色后,我们重新审视这一被人忘却的往事,倒不难看出它原本隐含的价值。
达盖尔在近两百年前发明的摄影术,从艺术角度看它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能摹仿绘画的效果,而在于它为人类增添了一种新的视觉体验。它与绘画的视知觉过程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画家面对的是一张白纸,如果他想将世界(主、客)复现在纸上则必须经过手的动作。生理条件和心理的经验差异也必然随之再现纸上。而摄影由于受与人眼构造基本一致的镜头的决定,使摄影家必须直接面对世界和直接再现世界,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人们接受方式的不同。绘画的魅力是人们面对画家高度情感化了的“自然”,而摄影则需通过“纯粹”的自然来感受自然。画家是把自我的激情和生命的冲动融注到画中;而摄影家则是把自身又重新抛回到自然,并在自然中和这个行动中肯定自我的存在。所以,摄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客观的艺术,它的本质是现实主义,也即所谓的“自然主义”的,而且这一独特的本质特征,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认知的其它艺术不能比拟和替代的。
李晓斌是中国摄影家中第一个明确提出以摄影独有的特点来表现生活与自我的人。虽然在此之前,人们曾多次,包括第一回“自然·社会·人”展览的前言中都提到过用“摄影独特的语言”来表现摄影,但那不过都是说摄影的一些造型规律,如影调、线条等,都不是在美学意义上的艺术特征范畴里。就我们所知,在世界上第一个明确意识到摄影这种优秀的品质和力量并把这种认识成功地变成现实,并为人们所接受的人物,是二十世纪的摄影巨匠——法国的尤索福·卡蒂埃·勃列松。虽然,在此之前有一系列的摄影家在实践上成功地表现了摄影这一品格,如斯泰格力兹、艾格特、斯泰申等。由勃列松和其它大师们倡导的这一纯粹的摄影运动,直到今天仍在显示着它迷人的风采,保持着二十世纪摄影发展的一股主导力量。与这一切相对照的是,摄影这一舶来的艺术在中国的命运,是它几十年来一直被消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禀性中。它接纳了早期西方摄影中的绘画意识,并具体地把它消融在中国古代文人画的意蕴中,这是抗日战争前的主要现象。抗战以来,由于所谓“革命现实主义”的影响,摄影则又开始强调它类似于其它艺术的古典美学的“典型化”意义。从本质上说,摄影与绘画的创作规律就并无什么不同,只是比绘画来得简单、快捷。不管抗战前后的表现方式有何不同,它们实际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上的默契,强调自先秦以来“诗言志”的情理思想。在这种思想强下的艺术,最后发展的极端只能是进行教化的政治工具。读者和观众的审美体验也将被其压抑或强奸。李晓斌郑重声明他不想对作品和人物进行褒贬,并坚信读者更高明。这种似乎令人无法忍受的“冷漠”态度,在弥漫着这样一种文化气氛的湖面上投下一块石子,引起轩然大波自是在情理之中了。
二十世纪艺术的一大特征就是对古典美学风范的反叛,使人们被异化的审美心理结构重新调整到没有禁忌的原始自由状态。这一转折的背景是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和因此而产生的哲学观的嬗变。人们对自然与社会有了更新的认识,更为珍惜自己生命本体的存在意义,追求肉体与精神的和谐和统一。艺术神圣的光环逐渐暗淡无光,因为每一个人都开始感到了自己的神圣。所有人类创造的客体不再神秘,神秘的是生命主体本身。当人们仍津津乐道地探求“影艺”时,李晓斌大胆、冷静地把镜头重新瞄准了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疲于奔命的芸芸众生,从而寻求建立自己与他们之间一种全新的关系,寻求“真实自然”的表现。这在今天看来,是十分难得的,它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对摄影的认识,是一种更为深沉的艺术态度和更高一个美学层次上的觉醒。李晓斌后来一直沿着这条充满个性的道路走了下去,拍摄了大批颇具人生高度的作品,并成为新时期摄影的代表人物之一。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张艺谋。他是以一组四块如广告牌巨大的作品展示自己的创作的。每件作品均以年号为标题,表现近年来我们民族坎坷的命运与个体存在之间的关系。它们无疑是一组对生命、对生活充满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激情的咏叹。比如标题为《一九七九》(可能有误)的最后一张作品,画面大部留白,只是在底部有一串如新石器时代似的彩陶纹样的人物形象,象征着人们迎着光明自由走去。而第一张标题为《一九六八》的作品则是一个荒野凋敝的山村小庙,凄然地挤在一大片黑暗之中。小庙中蜷曲着一个整个躯体都沉郁在痛苦和孤独之中的青年。四张作品都透射着对人生苦难与追求的思考,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值得称道的是,张艺谋在这组作品中以工整而又不失大气的手法表现出他以摄影审视生活和表现自我的能力。这组作品所有的形象几乎都是在非情节与情节之间,含义既明确又宽泛,给观众的审美再创造留下足够的空间。
李晓斌是以他石头般出世的沉默来凝固他眼前流逝的生活的,而张艺谋却以刻骨铭心的激情来陈述他对人、社会的关注。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选择,恰好也预示了中国摄影后来的两大美学流向。
我们已经粗粗地巡礼了中国摄影在新时期伊始迈出的不大不小的然而却是真正的一步。“四·五”摄影运动以及由这一历史变革而衍生出来的一代摄影家和“自然·社会·人”的三回展览,给我们的今天留下了什么,启示了什么?是颇值得深思的。无疑刚刚过去的昨天是辉煌的,因为它和昨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同步的。今天呢?摄影作为文化的价值似乎被文化抛弃了。直至今日的各种低层次的问题争论如“工具论”、“抓与摆”、“新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之类,使原本阔步前行的我们又缓慢踏步了无数日夜。终于,人们在对这种现状的极为不满中,方才发现自身与历史的距离。可悲的是,几年坎坷培养了一些投机取巧的庸才,使中国摄影在文化上的品格大打折扣。现在的中国摄影已失掉了她头几年那种无论从质到量的深刻觉醒。早先领略风骚的一代摄影家或被昔日的光荣冲昏了头脑,或因原本就缺乏的文化素质而重走进困惑。摄影展览、刊物充斥着花拳绣腿的雕虫小技和无聊地迎合各种名目的商业大赛的平庸之作。这一切让所有真诚追求的人们感到彻骨心寒。中国摄影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新世纪必定会创造出一代全新审美心理结构的人。他们定当为世纪的新生吹响号角,就像当初的“四·五”和“自然·社会·人”一样。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重新回顾刚刚成为陈迹的九年前的“四月”的全部意义。
注:
1、本文写作于1988年春,发表在当年6月的深圳《现代摄影》杂志第14期上。另外,由于1988年印刷编辑还属于贴毛条作业方式,当时编辑将本文的一段文字错贴到其它段落,所以发表时出现文章逻辑的错位。这次重新发表,将错位的文字恢复到正确的位置上。
2、文内提到四月影会和星星画会两个展览,他们之间的时间顺序为“自然·社会·人”展览在1979年4月初举行,而“星星美展”是在1979年9月举行,二者有一个时间差。特意提此区别,因为社会上一直认为“四月影会”是受“星星画会”影响出现的,其实恰恰相反。
作者:鲍昆,摄影家、策展人、评论家。四月影会重要成员。曾担任中国摄影金像奖评委,以及多个国际摄影节策展人和学术论坛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