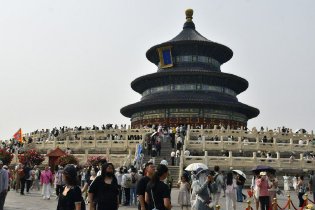月亮如一只肥胖的蛆芽,从浩瀚无边的黑暗土层中拱了出来。
雨刚才停了,月亮升起来了。当他们抬着那兄弟的尸体从屋门出来时,昆虫的鸣声淹没了没有边际的夏夜。
四个人推着木板车,悄无声息地,从一家又一家门前经过,极力不弄出一丝声响,可有些事情往往事与愿违。月亮以它微弱的光线照亮着正在发生的事。四兄弟背上被月光灼烧着,大汗淋漓。头发梢上集结着大颗汗滴,它们足够沉重的时候,跌落在脖子上,脸颊上。车轱辘上裹着烂泥,如被地层深处一只有力的大手牢牢钳着,让他们气喘吁吁。为了便于伪装,他们没用门板抬,而是用板车拉。车上盖着陈年稻草,仿佛能隐瞒一切真相。只有天上的月亮让他们四人感到极度不安。
人间,家家闭户大睡,没有人在今夜能发现什么。他们在泥水中的脚步声,车轱辘滚过烂泥发出的声音,响彻耳畔,在他们自己四周翻滚,一直跟随着,从没有离开过他们身旁半步;又在夏夜的虫鸣声中被淹没,消解。
他们在黑色的月光下艰难地行进。
丘陵上,一个偏僻的乡村,在外县接壤处的最西部。在乡村的一个菜园旁边,它,在几丈远的一根草秆上,晒瘪了,跟膆囊一样,软塌塌地挂在那里。经过了日晒和夜露,没有发芽;在微风轻抚中,在刀光一闪离开身体的一瞬间,独自垂挂在那里。完全是被动地接受着,它作为身体的一部分离开后,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
一只黑狗走上大路,它漫无目的,嗅着脚下,走走停停,偶尔抬起脑袋,望着远处,那里还有另外一座村庄。远远望去,看到的是人家房屋的墙壁和村庄外围堆放着的草垛——它没有看到熟悉的身影。
黑狗走向那座村庄。它没有结伴,仅仅是它自己单独而去。超过那条界限,它已嗅不到自己和同伴之前留下的熟悉气味。它低头嗅着地面,一些陌生的气息里夹杂着一缕甜蜜的味道,它低声赞叹了一下,用前爪扒了扒草丛,使劲嗅了嗅,那是它曾经的爱侣的气息。它要进入另一个领地,打败所有的公狗,才能见到它,得到它。黑狗在大路口站定,望着不远处的村庄。
它在犹豫。
随后黑狗在草丛边坐了下来,望着那个村庄。又回过头望了几眼来的路上——没有一只狗。要去的话,它只能冒着风险独自前往。
终于,踌躇半天后它下了决心,从大路上下来,来到村庄边。在村庄外逡巡。它紧张地端坐在一处,一有动静就从坐着的地方走开,回到有青草遮蔽的深丛后面。后来,它无意间走到茂密的菜园里,习惯性地嗅了嗅菜垄,一缕非同寻常的气味钻进他的鼻腔,让它咽了一口口水。它抬起头,微风吹来,它嗅到了食物的香味,那是挂在不远处晒瘪的鸡膆一样的东西。黑狗顺着气味走过去,从草秆上拽下来,一口吞吃了它。
车子终于在泥泞中驶出村庄。
车子从树顶覆盖的村庄中出来了。月亮在一块黑云中躲了起来,似人在云层中偷窥下面发生的一切,它更真切地看出四个男子的慌乱,他们手上和脖子使出蛮劲时爆出的粗结。车子如此滞涩,载负着沉重的魂灵。脚步也如此滞涩,每一步落地,就如一根铁钉子钉在地球上一样,要斜着身子晃动一下,才能拔出。一路上他们吃尽了苦头。
他们终于走到那丛黑色的石榴树下:“哎!我要,歇歇!”最小的老弟顺势坐在石榴树的刺丛下面。他的屁股刚落到石头上,二哥的声音就从头顶上响起来:
“你在赶集吗?!”
“我都累死了。”老弟扬脸回道。
“我们都不是人?!”
旁边的兄弟强压着愤怒向他低吼。他一机灵赶紧站起来,被脚下一团黑色的死狗绊了一下。他们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兄长身体的一部分自从离开他之后,此时此刻是离他最近的一次。
凭借熟人熟路,他们顺利上到村庄一里外的独板桥上。
一阵风吹来,路旁还未成熟的稻田在月光下扭动着波浪。或许是刚刚顺利走过最要小心的石桥,有人稍稍松懈了些。在没有任何迹象下,他们的车子像是抹了油一样,顺滑地掉到了高坎下面的稻田里。稻田里的波浪在那一小块地方突然停止了脚步,它们被惊吓到了,愣了一下,为那从天而降的一具尸体和车子。片刻之后,在黑色的月光下,稻田里的波浪又扭动着腰肢一下子扑闪到另一边去了。隔壁一块田里的电线杆上,电流走过时发出急促的呛呛声,警告着夜晚和月亮下的田野。
四个人站在路面上,即刻仿佛轻松了起来,身旁的巨大累赘,自动离开了他们。他们现在两手空空什么也没剩,连一根稻草也没抓在手上,什么也没有!跟什么事也没有一样,他们仿佛就可以这样空手而归。老弟站在他们旁边甚至抬起胳膊拍了拍手上的泥巴,被三哥一巴掌打了下去:
“你准备拍拍手,回去了?”
他们欠着身子伸着脑袋,去看田里那堆掉下去的东西——去他妈的!管他呢,就让他在田里烂掉算了。
四兄弟就这样一身轻松地站在原地。他们欠着身子,站了那么一会儿。终于有一人最先清醒过来——接着将有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他们。他们要大费周折,把他从稻田里捞上来,重新放到车里,抬到路上。巨大的恼怒汹涌而来,他开始大骂起来:“你瞅瞅,他还学泥鳅呐!还想钻到田里去。也不看看自己长得怂样!”
“不要再蠢了!”另一个喝止。
“活受罪,还要从田里把他抬上来。”
“他溜得倒是快呃!”
“哎!累死了,真想回家了。”
“不要再说了!你个蠢货!”
似乎是停顿了一下,他们纷纷从高坎下来,走进水田。倒扣的车子从田里翻过来,太重了,只能先把车子抬上去。又从高处下到田里来,抬着脚和胳膊,把死人从田里抬到路上去,放到车上。稻草还是要从田里收拾起来,覆盖在车里的尸体上,仿佛这才是万无一失的做法。这时候,竖插在田里的电线杆发出“呛呛”的声响,声震耳鼓,跟打锣一样,让每个人的头发都根根竖起。此时,他们最怕碰上赶夜路的人。
夏夜往往有赶夜路的人。丘陵上的一户人家这年冬天要嫁女儿,他们准备在夏季农闲的时候把女儿的嫁妆打好。这天木匠许成昆刚好给人家打完整套家具。当天傍晚结账,他受邀在东家喝了酒。吃完晚饭,天已经黑了。
刚出门的时候,天还下着小雨。走过官亭小镇的时候,雨停了下来。还没走出多远,一丢丢月亮从天边悄悄出来了。夏季的夜晚,一个人走在野外也不孤单,昆虫的鸣声一浪高过一浪,有独唱也有和声。木匠走在夜晚的原野上也高声唱了起来,他唱起庐剧《十八里相送》,唱到入迷的时候,木匠还回转身对着空空如也的身后说:
“梁兄,请!”
他背着锯子,斧头,刨子,凿子,墨线盒,和固定器人字叉。雨停了,他一只手还在空中举着伞,另一只手捏着桃木四方丈尺,桃木是辟邪之物,保护着他,让他走在最深的夜里,也不会担心会撞上什么。木匠走走停停,和他一人分两角中的另一个自己对唱起来。夜空之下是他一个人的舞台。《十八里相送》唱完之后,他站在路旁撒了尿。站在一旁扣裤子扣子的时候,他想起来,他应该把《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出戏全部唱完。戏文全部装在他的脑子里,他和他的剧团演了不下百场,他一个字也不会忘掉的。他一个人热热闹闹地一路走来了。银河的光带在最遥远的天边,月光忽明忽暗,流动的舞台,一个人的演出。
从小路转到大路的时候,他唱完了整出戏。在一个路口的树丛边看到一块石头,他走过去坐了下来。想到以前自己男扮女装唱戏的场景,禁不住唏嘘起来。坐在那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仰头望着天上。天上的银河,依然在那最高远的地方,用一条晦暗不明的光带显示出来,告知坐在夜晚原野里的木匠,它此刻的存在。
他最爱的草台班子剧团解散了,他们从南唱到北,从东唱到西。他识字不多,却是能背得了所有的戏文。人们扛着板凳,背着小孩,搀着老人,从一个一个村庄走出来,走在长长的小路上,来看他们唱戏。有一年春天,一个小城里的妇人一直跟着他们的剧团。她长得很漂亮,烫着弯曲的短发,穿着一件好看的蓝色毛线衣。跟了他们三个月,就是她丈夫找过来了也不回去。那时候天气也好,阳光照在土路上,路旁田里的油菜开始抽薹开花了,田沟里的草也绿油油的,都含着笑。沟渠里的水哗哗地响着,一路欢畅。他们欣喜地走在路上,有多荣耀,田间干活的人都停下手头的活计,手搭凉棚远远望着他们走过去。他们都走过去那么远了,还有人站在那里远远地望着。
他肤色白皙,骨骼小巧,旦角的扮相没有一个姑娘能赶得上。最后,他只演旦角。他优美的身段和扮相,谁还会相信他是男人?那时候,在这块地方,许成昆的名字,大人小孩都知道。现在他只能坐在夜空下举头望天——那上面真有水吗?人只有死了才能到银河上去吧。谁又能知道别人的事呢,在做活的人家说起来当年的剧团,他们都记得很清楚,那个一表人才的小生。而他就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只晓得他是木匠师傅。
木匠慢慢从石头上站起来,继续赶路。他站起来的时候看见一只黑色的死狗,卧在旁边,四肢交错搭在地上。当他站起来走开时,四兄弟才在稻田边铺好车上的稻草,拉起车开始往他这边来了。因为车子掉到田里,木匠和四兄弟错过了交汇。
木匠许成昆顺着路往前走,走过河埂旁一片小树林,一直往家走去。当年那些望着旦角许成昆远远离去的背影的人们,他们也不会想到,在许成昆成为木匠时候的一天深夜,他走过的路上,在小树林的另一边,在他刚刚离开之后,一场大戏正在悄然开始。
好像是为了弥补先前的艰辛,剩下的路,远离人群和村庄。路面没有那么多烂泥,长满了巴根草,不再那么泥泞难走。上完一段高坡,沿着河埂,他们来到那片小树林跟前——木匠不久刚刚才从那离去。小树林的一边是一片河滩。河滩才是他们的目的地。这里土壤松软,人迹罕至。
“你们听到什么了吗?”他们放下车子的时候,老二问道。
“没人喊你!”老弟很不耐烦地嚷嚷。
“我听到有人在唱。”老二伸长耳朵接着听。
“不要没事找事。干活!”
坑挖起来很顺利,胆子也放开了。月亮又悄悄隐到灰黑的云层里,只露出一点点;那高耸的黑云就如巨大的山峰,似有人打着灯笼站在下面,仅仅那么一星星光亮。他们就要干完一件大事,现在却几乎要虚脱了。他们个个全身都是泥水,衣服紧紧裹贴在身上。头发巴在头皮上,滴着汗水,跟滴着油一样。
事情快到收尾,蟋蟀好像在草丛中也开始为他们鸣奏。
“抬过来吧。”
“他倒快活,一步没走。”老弟对着大哥的身体嘟囔着。
“够深了吧?”
“再挖深些,不然他跑出来怎么办?”
其余三人瞬间同时停了下来,好像在侧耳倾听。
“哎呀!我就是顺便一说……”
“不要说了!你想吓死我们吗?!”
河滩里的坑又挖深了一些。他们停了一会儿,又有一阵风吹来。不知为什么,夏夜的虫鸣从远处传来,此处却静悄悄的;甚至能听见流星落下,划过天际的声音。月亮微弱的光,照亮一角,天空中的星辰在眨眼,下坠。
“我在哪儿?”在所有的声音都收拢起来的时候,突然有个声音在发问。他们所有人都抬起头,望向月亮,只有它一直在盯看着下面。
“不知道。”夏仓华举着头,从坑里往上走,望着天——突然,他摔了一跤。
“我在哪儿?”这时,他们所有人都转过头,对着车子停下的地方。
“他还活着!没死透!”夏仓华从地上爬起来。
“我的天啊!他有九条命!”最小的那个兄弟踩到放在一边的铁锹上,铁锹的木头长柄弹起来,狠狠地砸在他脑门上,疼痛的余波在空气中波浪翻滚,盘旋延伸。
“他还死不掉哪!”
铁锹被另一个人从地上拣起来,捉在手里,向车子那边走去。
“不要费事……抬过来!”夏仓华真是害怕他们再下痛手,特别是四弟那个蠢货。
兄弟们把他们的大哥从车子上抬起来,扔进深坑里,填土。
填土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一切:河水,树林,对岸,天上的月亮,村庄,他们刚才踩过的稻田,他们只想,快!快!快!快到自己最后一锹土!一切便都结束,一切才能重新开始!
两个站在坑穴对面的人,在挥土的时候,铁锹相撞,发出惊天动地的铁器碰撞的脆响。脑袋上面突然有扑棱棱翅膀飞过的声音,仿佛翅膀扑在耳根边,耳根瞬间滚烫起来。一切声音都混响起来。有哐哐的犬吠声,从远处村庄传来。还有轰隆隆的声音,像是大山坍塌了。鸣蝉拉起了它的长锯子,青蛙鼓起两腮,仰天长啸。远处的水田里传来几声田鸡叫:
“苦哇!苦哇——!”
河对岸传来了它的回声:“苦哇!苦哇——!”
一只瞎眼的蝙蝠从幽暗的地方飞来,它捕捉到了灵魂飞离躯壳的声波,它翅膀扇动带起来的阴风,刮乱了四兄弟额头汗湿的头发。
土埋了多厚了?下面怎么还有动静?土填进深坑,像是都被抖落了,一直没掩盖过身体,坑变成了无底洞。土不停地向四周倾泻下去,看上去那身体正从地下冉冉升起,也许有一条巨兽正在站立起来!
“啊!啊!我不行了!”有人腿抖得厉害。
“不要怕!不……要怕!马上就爬不起来了。”
坑穴结结实实填满了。土下面的人也不再受罪。他不再受到饱含水分的土壤灌满鼻腔口腔耳孔以致世界溃塌的极度惊恐造成的伤害。那压倒一切的惊恐之后,他感受到了万物的生命,土壤和水分中奇多生命的喧嚷。他在众生的和声中渐行渐远,一种关于活着的警觉性的东西,如开关一样“咯嗒”一声关了。一切都松散了,自由飘散,他向另一个终点滑了过去。他生于万物,又在万物的关联中离开,降落了,像一粒种子。
事情早有苗头。
末春进入初夏。阳光响亮,气温逐渐升高。植物在露水和日光下蓬勃生长。
一群白鹅在田间草地上吃草。早饭过后,夏家二媳妇挎着菜篮从鹅群边走过,如往常一样来到她的菜园。她走路没有声音,轻飘飘的,又极快。和她母亲一样行动敏捷,做事利落。她同样也继承了母系一方的心狠手辣。
菜园里,枝繁叶茂,覆盖了菜畦之间的小路。扁豆的藤蔓组成一垛墙;茄子宽大的枝叶向四周伸展;西红柿长疯了,和豇豆的长藤扯在一起,似乎忘了还要开花。辣椒在枝叶下闪闪发亮。粗壮的瓠子长在伞一样的叶子和藤蔓间。这些绿色植物里面能藏几头老虎。所有的蔬菜在气温和季节的催逼下几乎在一夜之间开花结果。丘陵雨季中,所有植物把在大地和季节中获取的能量都尽现了出来。
夏家的这位女人尽量放松,在植物众多宛如眼睛的绿叶之间,和更加闪亮的令人心烦意乱的果实中,保持镇静,但她分明在撷取果实时感到手心的灼烫。她分明看见在浅浅的水雾中,稻田的根茎在噼噼啪啪作响,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从地下升腾到空中。她年轻的心脏跳动加快。她在非分地期盼着什么,也在令人不安地担忧着。清新湿润的空气让她少许清醒了一下。她想起来,除了采撷蔬菜,还要割苦麦喂鹅。她从篮子里翻出镰刀,走到茄垄那里,苦麦菜舒展着绿长的叶子,饱尝雨水闪闪发亮,等待收割,好再次从根部长出新的叶子。
茄棵那里有动静!果然,有人在那些茄棵间等她在!在枝叶和果实之间有一双睁大的眼睛在紧紧盯着她,想要生吞了她一样。一切都被她猜中了,他又来了!竟然还在同一个地方,岔开两腿,一丝不挂,如一条凶狠的赤裸裸的蛇一样盘踞在草棵间。
他果然来了!那样大胆,那样不计后果。她嘴角竟然漏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心却又在顷刻间收紧了。那种隐隐约约的期盼瞬间变成一种明显的暴怒,速度之快令她自己也控制不了。她两头受难,两头都是危险的紧逼。丈夫的兄长步步紧逼,从来不曾松口,他似乎进入一种癫狂,他要跟她的影子重合,一刻不停地跟在她身后,不管走到哪里。
然而丈夫警告过她,在那晚之后。
那晚有多闷热!赤练蛇都从沟渠深洞里钻出来透气,它们红黑相间的身体,横卧在土路中间。没有一丝风,月亮也如烧透的红铁,挂在中天之上。她一个人睡在卧室的竹席上,解开衣服还是满身是汗。丈夫没睡在外面,他睡在凉床上,堵在堂屋门口。屋里太闷,大门敞开着。凉床死死堵在屋门口,他把着门看守,总不会再有事了。
半夜,丈夫睡着了。
就在半夜,另一个人又来了。他悄无声息地,从凉床肚下面,从板凳腿旁边爬了进来,爬到了她的卧室,她的床上。直至丈夫醒来站在床边。丈夫下定决心要中断这种事再次发生。他说过的话,他总会做到。
“你就不怕吗?”她提着镰刀弯下腰,苦麦菜割下去,发出呲嚓呲嚓的响声,断口冒出白色的浆液,这些白色的植物蛋白喂养着天鹅的近亲们,使它们在农家宅院里羽毛丰满,鹅冠红润。苦麦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它们无时无刻不在生长,又长了满满一畦。她一边麻利地嚓嚓地割着手上鲜嫩的植物,一边扭头对丈夫的长兄说:“起来吧!不然我也割了你。不要脸的东西,我已经给你缠够了!”她平静地对躺在茄棵中的人说话。生殖器的勃起如一棵肉树:“你来吧!”
“我一伸手就割了它!”
“来啊!”
女人果真直起腰,走了过去。没有一丝犹豫,伸刀下去。一股红色的汁液喷射到植物油亮的叶子上。叫声惊起一只鹭鸶,它从水稻田里飞起,腾空而去。那些正在吃草的白鹅,吓得腿一蹲,呆立在那里一动不动,继而伸长脖子低声絮叨着,互相安慰。等到第二声叫声响起的时候,它们半张着翅膀惊慌失措地跑远了。
她那样轻松,跟砍割一根鲜嫩的莴苣一样,根本没费劲;它挂在镰刀上,被远远地甩到几丈外的野檀树小枝条上。
那只黑狗吞吃了挂在野檀树小枝条上的东西,感到心满意足,它想回去了。黑狗又回到大路上,然后从大路上走开,在路旁石榴树下留下尿迹。它在那儿蹲下坐了一会儿,渐渐感到信心满满,便再次踏上了找寻爱侣之路。
这次它没有犹豫,从一个路口直接进入村庄。它看见了,它的爱侣走在一条村道上,它轻轻叫了一声,爱侣站住了,对它看了看,然后走了过来,在它身上嗅了嗅,它嗅到了爱的气息。当它们在为爱转圆圈的时候,一旁的草垛边突然转过来四五条狗,它们一起围攻无法脱身的它。这条黑狗擅入领地,它们不会原谅它。这是一起最残忍的搏斗,其余的狗咬它都咬累了。当它终于从爱侣身体脱离的时候,它变成了另一只狗,一只破破烂烂的黑狗。它艰难地往回走,当又一次走到石榴树丛时,它决定在那里停下,躺下来休息一会。不过,它再也没有醒来,只有微风轻抚它的皮毛。夜晚它差点绊倒了夏家最小的兄弟。后来,它又由硬变软,变质腐烂,它和它肚子里的肉块滋养了那棵石榴树,让那棵果树结下更大更饱满的果实。
菜园里的叫声,惊动了所有人。血喷溅到乌青的茄叶上,滴落着,汪在潮湿的地面上。场景骇人,没人愿意多看一眼。
长兄被夏家其余兄弟抬上门板,抬着去小镇医院的路上。
“我的蛋给弟媳割啦!”一路上,这位大伯喊叫了一路。当天凡是路过的人,没有人没听到他躺在门板上的咒骂,哭叫。他们轰轰烈烈地到达医院。医院只能缝合伤口,它被连根阉割。
跟在一起的兄弟们个个面红耳赤。
夏家在这个雨季名声远播,令人终生难忘地留在人们记忆深处。还有多少似曾相识的,在人海深丛中被煞有介事地抖落出来的欲念?是它塞满了耳朵。流言长出繁茂枝叶,充实午后昏昏欲睡的头脑,但哪一次有这样惨烈?
从医院回到家,长兄睡在他自己的光棍屋子里,日夜诅咒喊叫。大家都没法睡觉。他想激怒每个人,他在自寻死路。三天三夜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停止喊叫,咒骂,只是声音越来越小。兄弟们聚拢来,他们要在下一个夜晚来临之后了结他。他们真是受够了。平日,没有一个兄弟是哥哥的对手,他异常结实。只有一米六五的身高,却能举起带棱的最大的石磙,绷起的肌肉如钢板。谁也不要去惹他,他对谁也不会客气。三天三夜过去后,他的钢板从肠胃,从血液,从肌肉中撤了下来。
秋天水稻收割的时候,稻田主人提刀站在稻田中间,还是能看见被压倒的那片稻秧的痕迹。那块地方青棵被压断,生长受阻,变得稀疏。他忆起当初看见稻田被毁坏的痕迹时自己的暴怒。那时候,水稻正要抽穗,被毁坏的印迹鲜明,一片狼藉——水田里被踩踏搅浑的水还没泛清。现在,稻田里的足迹清晰地留在那里,早已变干。他站在那里,突然感到时光悄然流逝带来的忧伤。
他们在河里洗尽泥污,刷了车子,在晨雾中离开。回来的路上,四弟突然说:“怎么只有我们三个?还有个呢?”
“你昏了吗?!”老二低声吼道。
“不是,我们一直不都是四个人吗?刚才不也是吗?”
“你鬼附身啦?!”
“我是感觉我们有四个人在推车啊?!”
“不要说了!”
“这事情或许还没完,不是我想的那样!”
带着浑身疲惫,夏仓华走到自家门口。晨雾在墙头、大门边缓缓流动。他看见,从妻子的窗台边走过一个身影,是兄长!他没有埋在河滩上,他又回来了!并且在他们之前到达。
月亮又一次从夜的黑色沃土中升起。
丘陵沉陷下去。人们,早出晚归,春播秋收。一日三餐。阴晴圆缺。都归于井然的序列中。只是,风总是吹来,吹来另一个老光棍的风流史,大地便变得更加丰盈,草木更绿,黑色块状的村庄更加贴切。
站在丘陵高处,放眼望去:长长的大路,不远处有一片石榴树丛,已经长成小片树林。孩子们在树下踮起脚够摘果实。一个孩子不知为何,从树下走开了,走进深草丛中。他看见草地上有一根四方长尺,他好奇地走过去。不止这个,他看见草地上有一柄斧头,一头锈铸在土里;还有刨子,刨子被草根吸住,像被刨出的刨花一样,有一撮草从刨口中长出来。一个墨斗,在稍远处,歪倒在一旁,阳光平静地照在它身上。他看见这么多东西,想大喊一声,告诉同伴们,可他什么也没说。他站在那里,放眼望去,阳光也照在河滩上,河水在静静地流淌,泛着波光。
一只黑色八哥在孩子们的脚下啄食晶莹剔透的红籽。第二年,又有许多石榴树幼苗从鸟粪中长出。
作者:东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