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系列回顾继续,今天带来的是年度作品之一,英国作家林德尔·戈登的作品《T.S.艾略特传》。书中完整介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杰出诗人T.S.艾略特的一生,译者许小凡的精彩翻译更为本书增色不少。T.S.艾略特曾在诗中写道,“战胜时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穿透它。”相信这本属于诗人的传记也会穿透时间,传递到一代代读者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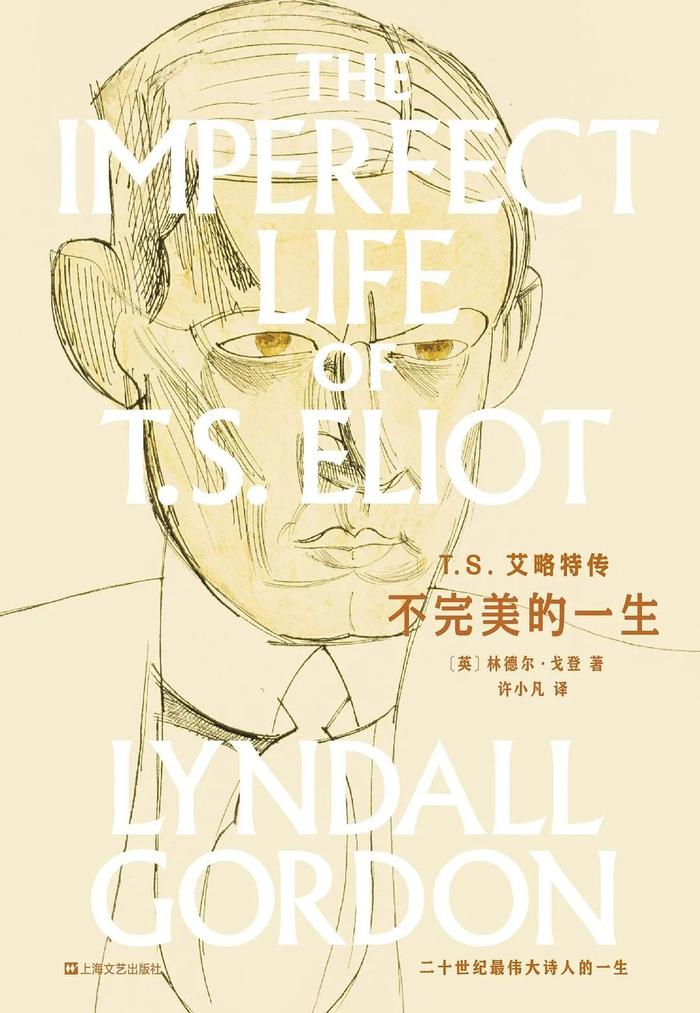
《T.S.艾略特传》
[英] 林德尔·戈登 著
许小凡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少年楷模
(本文摘自《T.S.艾略特传》第一章)
1888 年 9 月 26 日,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出生在密苏里的圣路易斯,父母分别是圣路易斯的商人和新英格兰的中学教师。三十八年后,他在英格兰一个小村子里受洗,加入英国国教教会。但面对着一颗与外在几无相关、常年隐于语言建构的表壳下的动荡心灵,这些事实对我们了解他似乎毫无帮助。在为艾略特画的肖像里,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将他的脸画得像张面具,唯有这样,才可能在这张不苟言笑的面容上突显那微阖、内省的双眼,在深色西装滞重的线条下勾勒出他肩部骨肉的轮廓。而据弗吉尼亚·伍尔夫描述,在艾略特苍白凝重、斧凿刀刻般的脸上,一双淡褐色眼睛活泼得出奇。

▲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 年 9 月 26 日 - 1965 年 1 月 4 日)(通称 T·S·艾略特),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诗歌现代派运动领袖。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代表作品有《荒原》、《四个四重奏》等。
仰慕他的人津津乐道于这面具人格,诋毁他的却要揭开面具,只为搜寻底下的缺陷:他们都没有看到的是,对于这个惯走极端的人,德行与过错几乎不分彼此。这个忠于“我们心中的自我”的青年在 1925 年还默默无闻时就下定了不为自己立传的决心。他恳求身边亲密的人保持缄默,也将许多信件封存至下个世纪。但与此同时,他也构想着自己的传记,在接连的诗作里浓墨重彩地刻画一个将自己的人生看作灵魂求索的形象,全然不顾与宗教格格不入的时代基调,不顾来自女人、朋友与其他职业令他分心的召唤。他曾提到一个努力向自我解释“一系列事件在信仰里最终达成”的人,在一封 1930 年的信中也写到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即尝试探索灵魂自传(spiritual autobiography)这一在二十世纪已经失传的文体。
艾略特希望成为“通过强烈的个人经验传达普遍真理的那一类诗人”。在一定程度上,他的作品的确保留了个人经历的“一切特殊性”,尽管要从作品回顾他的生活就只能借由想象的再创造,或《荒原》(The Waste Land)手稿中弃用的残篇,或最具自白性的剧作《家庭团聚》(The Family Reunion)的十个创作阶段。这个过程的主要困难,在于洞察诗人生活与作品间的联系,以使他主要作品的伟大之处得到彰显,因为这些作品同时也是诗人生活里最重要的现实。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脑海里描绘出一个对不朽充满渴望的人,并重构他借以通向不朽的谋略。在这非凡的谋略里,献身出于自愿,疑虑常获指引,专注又矢志不移;那一以贯之的纯粹轨迹于是浮现于我们面前——在这纯粹背后,则是几段因此而破碎的人生。
艾略特在世时,人们将他看作二十世纪的道德良心,但随着二十世纪逐渐淡出视野,问题也接踵而至:他诗里震颤灵魂的伟力是否还能让我们对他的为人保持宽容——比起和善的面具给人的印象,他有出人意表的古怪与偏执,在谜一般功成名就的生涯里又显得益发不可捉摸。艾略特去世近五十年后,他的全部文稿终于得以解禁出版,其中包括大量的通信。书信让我们看见他走向皈依的心境,征服文坛的手腕,婚姻困局的全景,偶尔发作的偏执与时而自笔端流泻的狎亵诗。皈依国教两个月后,艾略特在与出版商杰弗里·费伯的调侃中称赞斯威夫特式的狎亵诗体现了对恶的警惕。以此观之,“波洛王”诗——这与极少光顾他的完美恰好对立的“仇恨”或“生活之怖”——是否也应纳入艾略特所称的“范式”?在艾略特这里,我们必得沿着艰难的道路,穿过遍布“过失” 的密林。会不会恰是因为他承认自身的失败,承认他无法企及毕生渴慕的完美生活,才让那些巨作显得益发伟大?
艾略特的笔记与其他手稿诗(在他去世三十年后出版)表明,早在 1910 和 1911 年的学生时代,艾略特就开始以神圣的追求度量自己的人生了,他的转折并非发生在接受洗礼的 1927 年,而在他初次对圣徒的内心驱使、苦难与成就发生兴趣的 1914 年。艾略特在后期似乎离群索居,退守至祷告与修会的规律生活,但早年的手稿却披露了他少年时代对拥有圣徒的崇高使命的梦想:他渴望依凭自己的灵视(vision),而这灵视中的幻景已远远超出现世文明想象力的边界。
居于这隐秘生活核心的是对神迹(sign)的追寻。皈依七年后,我们在英格兰的一处花园里与他相遇,在这里,学生艾略特在 1910 年 6 月间漫步波士顿街头遭遇的神迹重又复苏。这一神迹穿透嘈杂的市声,穿透感官知觉,带着对永恒“真实”(reality)的直觉穿透时间本身。艾米莉·狄金森称之为:
那将不朽充盈的
巨大实体
由永恒向几个宠儿
暗暗启示
艾略特没有为之冠名,不愿使其落入不足以传达唯一的道(Word)的言筌(words)。但他无疑了解那无法命名的有多么重要 :他简单地说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值得人们为之而活——“除此以外,别无所有”。这样的坚信也让他认为日常生活不过是无谓的消耗。在《荒原》里,荒原之荒是一个地方,一座充满绝望的居民的城市。在后来的《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里,荒原之荒则变成了时间,神迹显灵的时刻之间“虚度的、悲苦的时间”。
不管荒原之荒是地方还是时间,它都表明人类无力理解神迹。这自然又让艾略特对人类卑下的处境厌恶不已。此后他经历了一场不幸的婚姻,又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在他眼里肮脏败坏、灵魂空洞的伦敦艰难谋生,这些都让艾略特更加确信人的可悲可怜。他笔下的伦敦像《序曲》(‘Preludes’)中的波士顿一样污糟不堪,但这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客观对应着他灵视中那个私密幻景的崩塌。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艾略特
人尽皆知的恶心就并非寻常的精英主义,而是更为奇特的灵魂的恶心。
艾略特在他的诗里最为坦诚,这份坦诚总受到著名的去个人化理论(impersonality)的掩护,虽然他承认这理论也有点言过其实。我们对艾略特的生涯越了解,以下这一点就越明白无误:变幻的面孔、嘈杂的声音——艾略特诗歌里这些“去个人化”外壳之下隐藏的,往往是对他个人经历的如实重构。艾略特曾写道,存在一类“作者的人格,或在更深意义上作者的生活向人物内部的渗透”。本书将对艾略特的诗歌与生活叩其两端,以追溯其诗歌中的自白性。它可以被称作一本传记,但却是艾略特意义上的传记。每当艾略特书写他人的生活,他总是较少关注外在的历史与境遇,而更关注那些他称为“不经意的”瞬间。“一刹那果决献身的勇气,”他在《荒原》中写道,“我们就凭这一点,只凭这一点而存在。”这本书的确描述了诗人生活的外部事实,但这些事实仅用以支撑那些塑造他作品的内在经验,后者对他来说才是决定性的。只有精简关于生平的琐碎细节,才可能勾勒出艾略特事业轨迹的延续性,将诗歌与生活看作一个整体图景中互为补充的部分:这个整体图景,就是诗人对救赎九死不悔的追求。贯穿他一生与创作生涯的,是艾略特对灵魂传记崇高情节的不懈践行。那是在《出埃及记》中就奠定了的情节:逃离文明,在荒地上经受漫长的苦难,随后进入应许之地。用繁冗的细节遮蔽这主要的故事情节无疑是南辕北辙,这也是为何对艾略特来说,一份巨细无遗的传记并不适用于理解他的人生。
叶芝曾说,一个诗人“从来不是那个坐下来吃早饭的、零散事件的集合体,诗人在思想里重生,是有目的的、整全的”。至于这一以贯之的思想如何产生,何时产生,很难有确切答案,但就艾略特而言,来源之一显然是在美国度过的少年时代里身边的人物。那个艾略特诗中挥之不去的幽灵般的楷模可以追溯到被爱默生称为“西部圣徒”的艾略特祖父,追溯到他母亲崇拜的那些身兼真理与美德的人物,以及麻省的安角上饱经沧桑的渔夫―这一切都塑造了艾略特的想象。晚年的艾略特渐渐看到自己诗中超越英国性的美国特征:“无论是出处,还是情感的泉源,我的诗都来自美国”。
艾略特提到过自己成长过程中曾把世界分为“艾略特家的人,艾略特家以外的人,和外国人”,艾略特一族中最伟大的则是他的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神父(William Greenleaf Eliot,1811―1887):“一个人所能实现的最大成就便是光耀门楣,当然要是祖父已经是个‘伟人’,要达到这个目标也就不可能了”。这位孙辈从未“挨打”,实际上,作为七个儿女中的小儿子,他反倒受了些“溺爱”,只是他从来感受不到自己的分量。
艾略特的父母在他出生时都是四十五岁,在他眼中像“先祖”一样遥不可及,他亲近自己唯一的兄长、长他九岁的小亨利·韦尔·艾略特, 以及长他十一岁的姐姐玛丽安。他们的父亲亨利·韦尔·艾略特(Henry Ware Eliot)风度高雅,喜爱艺术与音乐,嗅觉敏锐。他就餐前有先闻味道的习惯,也能嗅出五个女儿里谁拿了别人的手帕。他靠批发食品杂货起家,后来在生产醋酸的生意里破了产。尽管最终靠制砖东山再起,但他始终活在父亲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的阴影下:他的父亲拥有过人的经济头脑,人们常说若非他受到感召领受神职,那么密西西比河西岸的一切都将归他所有。亨利的自传并不以想象见长、其中呈现的是个埋头苦干的人,颇为自己的勤奋与孝道而自豪。他刻意为之的时候也有活泼的一面,比如在孩子的煮鸡蛋上画鬼脸。他夸艾略特是个谦逊温柔的孩子,但从不夸他有前途,因为他成绩平平(大多得 C),看不出有什么潜在的天分 ;这让艾略特“气馁”极了。
母亲对他的关心或许要多得多。她对他平等相待,他则对母亲报以热爱。后来,悲惨的婚姻把他和母亲隔绝开来,艾略特在阴沉的英格兰捱过战争年月,回忆里却是圣路易斯家中天花板上跳动的壁炉的火光,他躺在床上,母亲挨着他,给他讲《小裁缝》的故事。现有资料里,艾略特最热烈的情感表达来自一本《联邦群像》(Union Portraits)的扉页, 他将这本书“连同无穷的爱”送给他的母亲。他情操高尚、居易行简的母亲夏洛特·尚普·斯特恩斯(Charlotte Champe Stearns)教育子女日善其身,“充分发挥自身每一样能力,遏制每一点恶的苗头”。
艾略特最初十六年生活的城市在世纪之交以商业欺诈、排污不力与硫化烟雾闻名。但他仍表示“我很高兴自己出生在圣路易斯”。后来每当他回忆起圣路易斯,首先想到的都并非它的污点,而是撇开这些不快的童年回忆 :密西西比河浩浩汤汤、沃荡动摇的节律(“河在我们之中……”),新年里鸣响的汽船,1892、1897、1903 年泛滥的河面上“满载死去的黑人、奶牛和鸡笼的货船”,和六岁的他讨论上帝存在、带着他去洛卡斯特街与杰斐逊大道路口一座本地天主教堂的爱尔兰乳母安妮·邓恩。“我喜欢极了,”艾略特回忆说,“灯光、彩色塑像、纸花、人烟,还有能踏在上面荡来荡去的包厢小门。”在七岁的艾略特与面带笑靥的乳母的一张合照上,他头上一顶神气的贝雷帽,脸上挂着淘气的神情,安妮抿着嘴,一手搭在自己的髋部。多年之后,艾略特在一首小诗里写过一个专擅耍把戏惹恼乳母的顽童金·张·比尔斯(Jim Jum Bears)——“可有哪位乳母被耍得四脚朝天?”这首诗回忆了童年艾略特和安妮毫无戒心的亲密:他曾说自己对她“十分依恋”。
 ▲密西西比河
▲密西西比河安妮带他去洛克伍德夫人私校——那时这类学校还被称为“妇师学校”(dame school)。1898 年,十岁的艾略特转学至祖父创办的史密斯学堂,转学那天,母亲为他穿了一身水手装,结果惹来男孩子们的嗤笑。还有另一桩在他描述里“难堪透了”的羞辱 :“一次聚会上,我坐在两个小女孩中间,觉得热极了。一个小女孩越过我……向另一个俯过身去,向她大声耳语 :‘看他的耳朵!’于是有天晚上我在睡前用绳子把两只耳朵系起来,但母亲过来把绳子摘了下来,告诉我耳朵会自己向脑后长,让我不要担心。”他躲着其他孩子的聚会:“我在街上不停打转,一直转到回家的点钟。”
艾略特一家住在洛卡斯特街。这是圣路易斯人不大喜欢的一片区域, 离栗树街与市场街上的酒馆和妓院都不远,而那时钢琴家们正在舞台的后间里将“破衣烂衫的散拍子”连缀成跃动的旋律。圣路易斯在世纪之交成了世界的拉格泰姆(Ragtime)之都,1903 年斯科特·乔普林(Scott Joplin)在这里上演了拉格泰姆歌剧。1904 年,一位名叫杜平的歌舞团经理人为当年的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举办了拉格泰姆全国大赛。拉格泰姆是最早风靡二十世纪的流行乐,也有美国学者称《荒原》(1922)当中的即兴片段也是一类拉格泰姆散拍,在一段即兴创作里连缀了音律与人声的碎片。无需置疑的是,鲍勃·科尔与约翰逊兄弟 1902 年创作的散拍乐《竹下》(‘Under the Bamboo Tree’)之后将进入艾略特在爵士时代创作的戏剧《斗士斯威尼》(Sweeney Agonisters,1926)。
艾略特一家的朋友大多西迁到较为安静的郊区,他又没有年龄相仿的兄姊,因此艾略特的童年少有玩伴,大多时间都用来阅读。他最喜爱的一位作家是爱伦·坡。十岁之后的两年他必须每周两次看牙医,他在候诊室发现了爱伦·坡的作品集,于是设法读完了整本书。1899 年 1 月 28 日到 2 月 19 日之间,他把十四期名叫《壁炉边》的号称“虚构故事、花边新闻、戏剧、笑话——大千世界应有尽有”的杂志带出了诊室。同样也是十岁上,在一家人共度暑假的麻省的安角上,艾略特认得出大约七十种不同的鸟类。艾略特患有先天双疝,为防止疝气发作,母亲禁止他从事足球和一切激烈的体育活动。“船长”给艾略特上航海课时,夏洛特常在一边陪同,身边还有一个给她搭把手的成年女儿,以防艾略特太疲倦或身上太湿、太热。艾略特则总是好脾气地接受母亲的控制。他的母亲拥有一类强烈的道德热情与雄辩的天赋。她像那些杰出的十九世纪女性那样拥有智性的热忱,也恰如《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亚·布鲁克那样,虽因性别与境遇无缘高等教育,却是个天生的学者。她渴望成为一名诗人,而在最小的儿子展露诗才后,她希望儿子的诗情或能弥补她自身的失落。在寄给尚在哈佛的艾略特的信里,她这样写道:
我希望文学创作能给你带来我曾奋力争取却从未获得的赏识。我向往大学课程,但不得不未满十九岁就开始教书。我中学毕业时成绩优异,现在已经发旧泛黄的毕业介绍信上称“这个女学生是个天赋异禀的学者”。但我学过的三角学和天文学在教起小孩子后就毫无用武之地了。我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夏洛特 1862 年从麻省的弗雷明翰州立师范学校毕业,自此辗转于各地教席——从宾夕法尼亚到密尔沃基,再到俄亥俄州的安提阿学院,继而回到弗雷明翰。正是在后来又回到圣路易斯师范学校教书期间,她遇到了在密西西比河上运输物资的英俊职员亨利·韦尔·艾略特,并在 1868 年嫁给了他。自此,她将精力倾注于不断扩大的家庭与地方改革,尤其致力于为青少年设立单独的拘留场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间,丈夫破产,她在附近的女校玛丽学院教书,独自养活全家一年之久。除了梳妆柜上的针垫之外,她房间的陈设全无传统女性的痕迹。朝阳的窗边放着一把舒适的扶手椅,虽然这椅子把抽屉柜给挡住了。床对面是张搭着丝绒的壁炉台,上面摆放一幅圣母子像。墙上挂着一幅刻着狄奥多西和圣安布罗斯的版画,画里的神圣权力正对世俗权力宣告胜利。
艾略特在皈依之际曾告诉母亲:“我坚信我们之间了解与相像的程度之深,或许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我也坚信我们(在来生)一定还会相见。每当我做出什么为人称道的事……我都会觉得那是你与我共同的成就。”除夏洛特之外,斯特恩斯一族没有出过其他作家,但赤诚的道德感却一脉相承。矗立在麻省斯普林菲尔德的“清教徒”雕像*表现的就是一位斯特恩斯家族的先人:他左手怀抱一本厚重的圣经,右手执握朝圣之杖阔步前进。夏洛特矜持寡言的叔父牧师奥利弗·斯特恩斯在哈佛神学院的讲坛上曾突然口若悬河、语惊四座。无论什么他觉得是真的,是对的,那么“天塌下来”他都要去说、去做。
将夏洛特的诗句与艾略特同读颇具启发性。她书写“预言家的灵视” 与“先知警训的呐喊”,也叙述上帝选民的人生转折:《无名的圣徒》中的使徒,以及圣巴拿巴和圣狄奥多西。她的主人公效仿着爱默生和钱宁这类十九世纪新英格兰人。他们是“沉迷于真理之中”、“醉心上帝”的个人主义者;她的萨沃纳罗拉、布鲁诺和圣方济各都忠于他们私密的灵视。她笔下那些自无底的深渊走出、手握崇高真理的思想者,与艾略特 1911 年到 1912 年间失眠诗里的主人翁如出一辙。
夏洛特的力量是布道者的力量。她诗歌的力量来自高昂的激辩与扣人心弦的描写。她的听众是那些“天赋异禀”、超类拔群的人,她所传达 的讯息则是怀抱信念渡过信仰的绝境:
你们绝望
不信救赎的,且看那光,
昏黯一时,却终要闪亮……
(《得救!》)
她有说教的天赋,但缺乏伟大诗人的创造力和鲜活的想象。她的儿子运用了同样的传统意象——那充盈她母亲诗中的极乐之光、欲念之火与涤罪之火,穿过“荒漠”的朝圣,与以季节作喻的心灵的干旱——却能避免失于流俗。在“濒死的一年”的绝境里,她的园中枝条僵枯,没有花朵,但一类新的力量正蓄势待发。“四月最残忍,”她的儿子将这样写道,“从死了的土地滋生丁香。”母子二人用同样的传统意象象征神恩。在《主之招迎》里她听见孩子的声音。钟声象征疑虑后重生的信念。而水——“天国的泉涌”和“医病的洪水”——则允诺着漫长苦难后的解脱。
夏洛特·艾略特描摹了人在失去与重获神恩之间的存在状态,她的儿子又用二十世纪的诗歌语言重绘了这心灵的地图。艾略特的作品里没有母亲的乐观与对神恩的确信,这也是艾略特与母亲的主要区别。他笔下懦弱的主人公 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感到应当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又回避了这个问题。虽然普鲁弗洛克缺乏勇气,但奇怪的是他又面对着许多夏洛特·艾略特诗中的问题:人如何直面“茫茫的空虚”?既然知道我们必死,那么人生是否值得过活?“就这样了吗,这个残缺不全的人生?”“我如何得救?”早在离开母亲之前,艾略特的心中就已拥有了完美生活的样本;更长远的问题,则是能否让这个范本成为自己的人生。
此后他将拥有的是双面的人生:公众面前,他是众人追捧的焦点;私下里,他却是讳莫如深的隐士,他的离群索居在闹市与盛誉之中又显得益发难以捉摸。一边是内心的岑寂,一边是足迹遍布欧美的演讲家。因长期惯于扫视台下成排的听众,他渐渐生出了一类众人瞩目之下内敛的神情。他的皮肤看起来紧绷在脸上,五官的轮廓锐利分明,又清秀纤弱——特别是稍稍内陷的嘴部线条。他生性惯于以重重的道德律令要求自己,以被世人遗忘的原则自律,就像所多玛的罗得与巴比伦的但以理——那些在他看来因无法行善而保持缄默的人。
他总是言说那些“不被言说的”,在公众面具保卫之下的孤独里过着隐秘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他是诗人,有探究并定义这种生活的需求,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他的生活。他的诗从生活的酒滓里滤出一出结局早已注定的大戏,呈现出的便是一部连贯的灵魂自传,诚恳,直接,比任何旁观者的考语都来得更洞明,更直指人心——他的生活与作品就这样紧密相连,彼此创造。这部传记就基于这些由诗人亲自作出的表述,并与他实在的生活相印证。
在一篇题为《风景对诗人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Landscape upon the Poet’)的演讲中,艾略特基于童年时东游新英格兰地区的深刻印象, 称自己为一名新英格兰诗人。海边的他总是那么快活。每当回忆起童年在安角的格洛斯特度过的许多夏天,他也总是十分愉快。
艾略特八岁之前,一家人每到安角都住在霍桑客栈 ;1896 年,他的父亲在格洛斯特城外的东角建了一座结实的大房子。他在 1890 年买下的这块地位于一片粗砺的野滩,四周环抱着丛生的野灌木,石板路直延伸到海边。房子顶层的窗户对着花岗岩海岸和海面上的白帆,从另一边向外看去就是海湾。在艾略特的回忆里,格洛斯特的海湾是新英格兰沿岸最美的几处之一。一张他哥哥亨利拍下的照片展现了世纪之交的一幅景象:张起风帆的捕鱼船队上桅杆高耸,俯瞰背后村庄里楔形墙板的房屋和斜屋顶。渔业从最初起就是格洛斯特人的主要生计。十七世纪,一位牧师与最初的殖民开拓者一起到来,对他们说:“我的弟兄,要记得你们行路到此是为了心灵得救。”而他的一位弟兄接着说:“也为了打渔。”在艾略特那时,在美因街与邓肯街的拐角上打发时间的渔民们常说起安角近海暗礁上的风暴与海难。冬季仍要工作的深海渔民冒着凛冽的寒风,从大帆船起航驾小渔船出海。这些小渔船常被掀翻,或在雪雾里迷失方向。传入少年艾略特耳鼓的,就是生还者口中那些惊人的险境和渔民的顽强与坚忍。
艾略特早在中学时代的作品中就赞美渔民习焉不察的自立与壮举, 这些内容也贯穿他整个写作生涯。1905 年 4 月和翌年 6 月,艾略特在《史密斯学校纪事》发表了《鲸的故事》与《他曾为王》,并在故事里得意地使用了航海的行话。后来的《玛丽娜》(Marina,1930)中,海风卷走了文明的渣滓,而救赎的爱―连同它的奥秘与希望―的苏醒则意味着冒险横渡大西洋,缓慢迫近新大陆,迫近微茫的新英格兰海岸、丛林与灰色的岩石。艾略特对先祖的想象就基于这些他崇敬的安角上的船长。在题为《绅士与海员》(‘Gentlemen and Seamen’,1909)的一篇文章中,他赞颂艾略特先祖一类的“平民贵族”——发迹于新英格兰沿岸村庄中的小镇长老、海员、小印刷商、零售商。他的曾祖父,老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曾是新贝德福德的一位船东,得到过一整套后来家传的中国“柳纹”瓷器餐具。艾略特脑海中时常闪现那些古老的肃穆面孔,古老的紧抿的双唇,来自宗教守则和在与贫瘠的新英格兰长期相搏里代际相传的古老秉性:牙关紧咬,不屈不挠。
孩童时期的艾略特在安角的海滩上寻觅着大海抛向岸滩的物什:星鱼、鲸鱼的脊骨、折断的船桨、鲎。这些水塘给他的好奇心留下了“更纤巧的海藻和海葵”。他曾经收集海葵,晾干它们,并给它们分类。十岁的时候,在一块多岩区域涨潮形成的水潭里,艾略特第一次透过水面看到了海葵。在他的回忆里,那次经历“对一个不寻常的孩子来说并不像看起来一样寻常”。
在此后的诗歌中,艾略特将随着对危机与启示的再现不断重返安角的潮水与海滩。在死生一线处“扬帆前行”的海员形象就以那些格洛斯特的渔民为原型,来自少年艾略特在安角度过的夏天。他的想象同样系于寂静的水池与盛满光芒的水:它们象征着回忆里无以言传的喜悦,这回忆永恒唤起着诗人,在他的诗句中不断重现。
原标题:《战胜时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穿透它丨单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