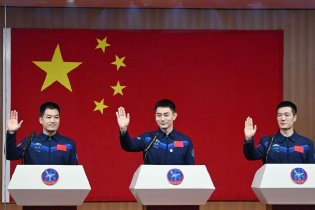文|李晓
我有一座城。这口气挺大的。
我确实有一座城,它安卧在我心里,等我一页一页翻开它。
这座城,奶奶是我的引路人。那年我14岁,夏天某日,“嘬、嘬、嘬嘬嘬”,这是我奶奶唤鸡的声音,她手里挎着一个竹篮,竹篮里是产自老家山坡上的金黄的玉米,奶奶要给一群鸡喂食。不过那天鸡们似乎敏锐地感觉到了,奶奶急切呼唤的声音里藏着什么阴谋。鸡们没围拢过来啄食,奶奶发火了,她猛扑过去,抓住了其中一只母鸡,其余的鸡受惊后扑腾起来,鸡毛落了满地。奶奶捉的鸡,是要到乡场上去卖了,供我到县城上高中。
鸡毛在那个农家小院里飞舞,一直飞了30多年,这也是我来到一座城里的时间。那年,我要到县城中学上高中,但家里意见不一。爸望着我,有些忧虑的样子。妈望着我说,就去镇上中学读吧,那里的皮校长,拐几个弯算是我的表叔。奶奶是我到县城中学上学的坚定支持者,我爸一向听奶奶的话,他朝桌子上重重一拍说:“这事儿就这样定了,送二娃到县城上高中。”爸转过头来,用威严的目光瞪着我说:“二娃,你不要给我丢丑!”
从此,我来到马路上每天都灰尘滚滚的县城上学,电线杆上的电线如蛛网密织。不过,县城临江的高中校园,被绿树葱茏包裹着。绝大多数同学来自县城,从他们的穿着就可以看出来。县城的同学在春天喜欢穿运动衫、白色运动鞋,来自农村的同学大多是蓝色卡其布料的上衣,每颗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
在县城,我只有一家亲戚,就是我的表姨。一个星期天,爸带我到表姨家去看看。其实表姨家住在城市近郊,院子旁有一棵大黄葛树,枝丫中透出苍穹云层洒下的光斑,浮现在墙上如皮影戏一般闪烁,夏天也很是清凉。表姨父是一家企业的工会主席,他把报纸糊满了墙,我歪着头看报纸上面的新闻。表姨父说,你要好好读书。我爸叹了口气摊摊手说,哎呀,这个二娃啊,学习成绩很一般。我爸这样刺激我。

17岁那年夏天,轰隆隆的雷声过后,滂沱大雨中,我家那山梁上的老屋在风雨里飘摇。云层里一道霹雳闪电,照亮了村里老侯家三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却照不亮我的黑夜。
我不是种地的命,我不愿意一辈子匍匐在泥土里。18岁那年的秋天,我通过考试成为乡里的一名招聘干部,3年签一次合同。我工作的这个乡,那时与县城还有一条大江相隔。浑黄江水日夜奔流的大江对面,是雾蒙蒙的县城,那里才有着我的向往。
那年,我两眼充血地写诗,用复写纸复写后疯狂投稿。有一次我到县城去拜访朱诗人,豪爽的朱诗人夸赞我的才华,还向我推荐了他在县城机关做一把手的一个朋友,用龙飞凤舞的字体写了一张便条,让我去找那人。
记得那是秋雨连绵的时节,我提着鹌鹑蛋、山核桃去找朱诗人的那个朋友。那人看了朱诗人的推荐信,轻轻地笑了笑说,这个老朱啊,以为人事调动是写几句诗那么简单啊!简单聊了聊乡里的工作后,他安慰我说,你还年轻,要安心工作。去县城工作的梦,就这样熄灭了。我也死了心,就在乡里工作下去。

在我24岁那年,县城扩容建设,江上大桥通车,我所在的小镇与县城连成一片了。而今,这座波光潋潋的城市,已成了一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在城市的硕大根脉里,我是缓缓爬行在上面的一个甲壳虫。我已经铁了心,与这座城终老。无数次从外地归来,我呼吸上几口这座城市的空气,恹恹的肺叶才一下青翠生动起来。
我在一个单位一直工作了三十多年,许多人说这是一个奇迹。在单位的档案室里,有我起草的不少公文,这是本职工作,供我衣食饭碗;我也创作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那是业余爱好,打发流水光阴。
我奶奶83岁那年进城和我爸妈一起生活。她进城时带了一把镰刀,以备随时割草用,还带了一个手电筒,以备走夜路用。这两样东西我奶奶都没用上,她87岁那年痴呆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她89岁那年,被我们驱车带回老家的山梁,我爸嘴里喃喃唤出村里的那些老地名:马耳坡、马鞍桥、侯家梁、乌龟堡、千口山、歪梯子……我奶奶混沌的记忆顿时被闪电擦亮了,她坐在石头上摇晃着白发稀疏的脑袋说,我不回去了,不回去了。我爸激动得满眼是泪。一年后,我奶奶那小小的坟,就立在故土马鞍桥旁边。

在这座城里,我们村里的几个老乡几年前建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它述说着我们真实的也带着矫情的袅袅乡愁。它在互联网的海洋里,飘着村子里的稻花香高粱红,让我们这些来自村里的人串在一根老藤上,再次感受着农历二十四节气里的风雨雷电。
在这座城里,这些年一路下来我结交了不少朋友,有的忽然之间一抬头才发现走散了、走远了,有的而今就靠在朋友圈里互相点个赞,有时一顿饭从春约到冬也没有兑现,都习惯了。有时突然发现几个从青丝一起走到白发的老朋友,心里最渴盼的就是那几口醇香的老酒填满莫名的“窟窿”,和其他人喝,喝不出那个味儿来。前不久在马路上碰见一个人,歪歪斜斜地走路,而后靠在小叶榕树上大口喘息,那是我结交多年的朋友老卢。
老卢患有高血压,有次喝了酒发作脑溢血,造成了偏瘫,治疗出院后靠不断康复锻炼才使病情得以减轻。那天,老卢见了我,嘴里含混不清地说,你、你是我的老朋友,我不会怪你劝我喝、喝、喝酒。
我轻轻地拥抱了老卢,他身上有着嶙峋的骨头,扎痛了我。
有一天,在一位老朋友的朋友圈里看到一幅图片,他坐在城市楼顶上怔怔地望着蓝天上的悠悠白云,发感言说,真想光着身子躺在白云里泡个澡。这场景一下把我融化了。在这座城里漂流与行走多年,到了眉上挂霜的中年季节,其实心里最想要的就是这样的天气,天高云淡,随心所欲地飘着,牵挂不要那么重、那么深,很多欲望也被风吹散了,大地显出了开阔气象,与人的内心贯通。
我有一座这样的城。我笑问这座城,它拥有过我吗?我伸出手,让它给我把把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