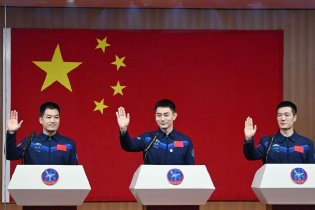(3)
江澜拨通章新宇电话:“江北开了一家叫“中原地带”的酒店,听说,饭菜很有特色,想去尝尝,要去的话,就咱俩。”
她以非常热情的口吻说话,但却没提生日的事。自从嫁给章新宇,她就不再敢提“生日”了,因为,这个日子恰恰是章显德的忌日。为保护章新宇那颗敏感脆弱的神经不受伤害,从此“生日”在她的生命中消失,又恰巧户籍上她那栏显示是大年初一,她谎说也就是这个日子了。可自己不愿意、也不习惯过生日,不老不小的,让人笑话。每次她这样搪塞。
电话那头,章新宇掷地有声,“我走不开,想去的话,自己找个伴,好吧?”
“那干脆我去参加同学聚会好了。”江澜横下心来说。
“也好,随你!”
江澜放下电话,一种被忽略不计的失落感袭来。
在另一间办公室,章新宇正与一家公司畅谈“合并同类项”问题。说难听点是大鱼吃小鱼。敞开了说是“吞并”。
“我们分头去走手续,在事情还未成型之前,请不要对外声张。以免搞得人心惶惶。也请欧总放心,到时你的员工暂且在原来的岗位上不动,有机整合后再做调整。有我的,绝对少不了他们的。”章新宇似乎对这件事的独立操作胜券在握,同时也忽然有了一种与江澜各自为政的成就感。
听章新宇把话说得如此得体漂亮,欧总顺势将了他一军儿,“有您这句话,我老欧没说的!别的我不担心,凭章总的能力,那是要风有风,要雨得雨,关键是你的头顶上还有一片天,到时可别让我枉费心思。”
“欧总,你这分明是看不起我。”
“倒也没那么严重,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的公司归你,一,从此后我省心了;二,你也是有利可图。从私人关系的角度讲,肥水不流外家是最好的,所以,促成这桩买卖,我是情愿的。两全其美的事儿嘛。”欧总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情。
这个欧总,大名欧天成,论年龄,比章新宇也就大个三两岁,可搭眼一看,差十岁不止。章新宇的头发营养充足,长势良好,再看对方,头发好比秋后的豆角地,基本罢园,只双耳之上还有些七长八短的毛发勉强支撑着地盘。
“哎呀老兄,把心放稳妥了,只要是我许下的事儿,没二话,头拱地也得争取。”章新宇用拳头象征性地捶了一下欧总的肚子。
“那感情好,我替1000多员工谢谢你!”欧总呷了一口茶,慢悠悠道:“要我说,这事儿也急不得。慢慢来。兄弟,你记着,就算没这事儿,我老欧也是啥啥不耽误,穿绸裹缎,吃香喝辣,咋舒服咋来。只是怕这身子骨不听咱召唤。趁这脑袋瓜还不糊涂,把事儿解决了,省得给孩子带乱。你说对吧?还是那句话,咱不急,你慢慢运作。这样,咱们今天贵宾楼小坐,我请客,怎么样?”
章新宇慷慨道:“来我这儿,哪有老兄张罗的份儿?!”此刻,章新宇的自我感觉很好,人在职场,成长是必要的。他想。
两人寒暄一阵,来到办公楼下,章新宇回转身抬头,见江澜的办公室没了灯光。此时的江澜已融入到推杯换盏的氛围中去了。不过,有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味。
“来,章总,坐我的车,”欧总话音刚落,后车门已打开,一个跟班谦卑地用手扶住车筐。章新宇坐了进去。挨着欧总。
“老地方,锦华!”
“好的爸爸!”女司机回头嫣然一笑。
女子的声音似曾相识。章新宇的思绪有些乱,极力在大脑记忆库中发动搜索引擎。难道是她?
这是一个娇小玲珑,礼貌得体的姑娘,和那天高唱酒神曲的女子大相径庭。一边感受着娴熟的车技,想像着她与路灯杆激情拥吻的样子,章新宇在心里笑。停稳车子,等大家下了车,欧总走上前来介绍道:“这是我的宝贝女儿欧兰!”
“您好章总!我们可是老熟人啊!”欧兰快言快语。
“没成想在这遇到你!” 章新宇很场面地笑。
“上天的安排,或者说缘分使然!”女子身体微倾,伸出纤细的手指笑意盈盈地:“请多关照!”
“好啦,进去坐下聊,怎好把客人撂外面。”欧总对女儿嗔怪道。
“这边,锦华厅!”宝贝女儿熟门熟路,一行人顺着女子手指的方向穿行而过。
“今天不谈公事。”一阵寒暄过后,欧总接过服务生手中的茅台,放在章新宇面前一瓶,然后慢声拉语道:“只、喝、酒!每人一瓶!”
章新宇对自己的酒量没有信心,以往都是江澜替他挡驾。今天单枪匹马上阵,不免有些心虚,所以席间,不住地推辞。钟一梅的一番话咋说的?他是她的坚强后盾。每当众人力捧江澜“巾帼不让须眉”时,章新宇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不管怎样,自己一男爷们,总得做出点事情来。谁掌舵不要紧,自己的能力人人见。这次的事情没有同江澜商量,他觉得不够光明,不是有意隐瞒,过一段时间,等事情初见成效再说。他想象着憋宝之后的效果,到时江澜会把军功章亲自给他戴上。
章新宇一边与欧总周旋一边不断宽慰自己,然后举起杯子同欧兰干了一杯。
欧兰很会说话,“我可要端着饭碗去您那里讨生活了。不求什么一官半职,只要给个位置能让从英国回娘家的小女子有个用武之地就行了!”
“你捧着金饭碗,什么样的岗位能满足胃口呢?”
众人捧腹大笑。
“说好不谈公事,兰兰犯规了!”欧总在一旁附和着:“合并后,让她去扫地!”
“老爸你真心狠,还没怎么样,就想把我扫地出门啊?”
“嗳,这我可说了不算,那要看章总是不是赏识你。”
“章总,看见了吧,老老爸专会设障碍。到时你得帮我。”
“欧兰小姐,像您这样的人才,得实行保护主义。”
宴会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进行着。
已是晚上十一点,一行人却还兴意盎然。
走廊里几个服务生在做清扫,扫帚拖把之类发出不和谐声响,向客人有意无意暗示着什么。章新宇习惯性地抬手腕站起身,“呦,可不早了,我看今天就这样吧。”都回去休息,今天——破费了,改日——我做东——”
突然,一阵急促手机铃声响起,章新宇从容地按下接听键。
“章总吗?我是你胡大姐,马上到和平医院!江澜在急救中心!”
茅台的后劲儿不容小视,章新宇酒喝过了头,脚步有些不稳。大脑还在反应当中,电话已传出忙音。
欧兰一行将章新宇送到医院时,江澜已进入CT室。江澜的闺中好友将就诊的医疗卡塞到章新宇手中:“交了五千,怎么说也够了,江澜刚进去,头部核磁共振,外加颈椎……”
“怎么,喝多了?”
淑琴没言语,眉毛向上一挑,伸出一根手指不以为然地指了指自己的方便面发型。
“头疼病又犯了?下午还好好的!”章新宇迷惑不解。
淑琴有些激动:“头痛加呕吐!我小姑子头疼仨月,呕吐不止,脑瘤,早死了。快给她好好查查,头疼是要命的事儿。”
章新宇被雷击一般,额头上冷汗直冒。心想,这人真是口无遮拦,水平到家了。“胡姐,你这什么话?”他朝欧兰尴尬地笑笑,催促道: “你快回去吧,别让欧总等太久。”
“那好,不再打扰,需要帮忙打个电话。”欧兰回转身用拇指和小指做了个打电话的姿势。转身离去。
江澜生病了,说病就病了,也没什么征兆。这事儿意新宇有点不大相信。她看上去很健康,连她自己都说呢,壮得跟头牛似的。
“啊呀,姐夫,你可来了,你瞧瞧,学会吓唬人了。”从走廊尽头的卫厕又钻出一个人来,未来到近前,炸耳的声音充塞走廊的各个角落,晃了几晃站定之后,夺人眼球的两只乳房还在呼应着女人的动作上下滚动着,要不是卫衣,恐怕就要跌到地上,此情此景,让人忍不住想像落地爆炸之后,汤汤水水四下迸溅的惨烈景象。
“她,喝酒了?”章新宇心急火燎,“感冒了,打了‘先锋’。这可是要命的!”
“亲爱的姐夫少安毋躁!”女子无力地摆手:“她,她不行,没喝,我们几个喝起来刹不住闸,差点被‘酒鬼撂倒’。”
章新宇虽没在酒桌上练出真本领,但凭“酒经沙场”的经验,他判断出这位“酒鬼”的状态离酒鬼不远了。
“放心,她,沾沾嘴皮子而已。喝酒——她不行。”女子口中喷出的酒气与章新宇茅台发酵后的气味没二样,
方便面解释道:“难得一聚,老二搬迁,逮了个理由,她倒好,还没起席就犯了病,纸糊的,不禁折腾。”
章新宇直后悔喝了酒。关键问题是还做了一件提不上桌面的事儿。这事被动了。喝了酒,就先让酒说了算吧。
江澜进急救室后,先打了止吐针和止疼针,用以缓解头疼和呕吐。主治大夫要求做头部CT,否则单凭口头描述,无法做进一步诊断。
在医生引领下,江澜被带进玻璃墙内室,又一步步挪到里边套间。此刻,血管迸裂的感觉又回来了,她浑身燥热,嗓子眼火烧火燎。站立行走,无所适从。很幸运,此刻她的头疼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现在可以叙述一下她的头疼史。
她与八十八个头疼患者交流过,很遗憾,他们之间找不到共同语言。人家谈论着头疼的问题,而她被理解为用头疼的语言谈论着头疼以外的事情。她时常被怀疑是头疼还是“头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头疼有八百种之多(神经性头疼、风湿性头疼、颈椎头疼、外伤导致头疼等等),没有实质性病变,天知道她属于哪一种。为了排除牙髓石压迫神经引起的头疼(这是新课题,以此为据写一篇论文,足以在权威杂志发表),她狠心拔掉一颗牙。别说一颗,两颗也不在话下,比起头疼,也就相当于薅掉了一根头发。
鉴于她的头疼纯属无理取闹,医生为她开润物细无声的药物,如谷维素。此药于一个顽固的患者来说,等于糖球,没事随便吃着玩玩。也有吃了之后,不疼不痒、以药当饭的,像脑清片、羊角片、头痛宁之类。当然了,有“杀伤力”大的:去痛片。她对此也情有独钟。目前来讲,唯有此药能把她从死亡线上拖回来。不能忘却的药是布络芬,服用过后又加一痛——肚子痛。记忆最深刻的是卡马西平,服用三天,牙龈肿痛,嘴巴成了猪拱子。一根吸管侍候一日三餐。但她很兴奋,因为排除了三叉神经痛。她始终记得医生棱角分明的脸和笑意盈盈的眼:根据影像,根据你的描述,根据你对药物的反应,你不是三叉神经痛。医生为她排除一道险情,感动过后,回家继续等待下一拨头疼。
她的头痛也许是全世界都在研究解决的一个新式课题。一旦发作,来势汹汹,濒临死境,强力止疼过过后,好人一个。再头疼,再见医生,医生断言她不是单纯一种头疼(江澜的理解是综合性头疼),兴许有遗传因素。啥都别说了,只有打止痛针。有时,打过之后和打针之前情形并无二致。
“还有杜冷丁。”医生跟江澜的脸要答案。江澜恨不得跑。
长期的摸爬滚打,江澜聪明了,她专心致志地在止痛片上下了功夫。一片不行就俩,再不行,继续加量。原来,事情如此简单。
这次,江澜来医院做无用功,完全是在两个闺蜜的撺掇下,谁知道她得了什么疑难杂症,束手无策,只得求助医生。
江澜早有预感,她的这种顽症会与她抗战到死。她心知肚明。
江澜被拥着进入了“密室”,她有点视物不清,只知道地当腰赫然蹲着一个庞然大物,侧身探出一张看上去宽敞舒服的床。她等不得大夫指令,立即侧身躺了上去。
头颈部固定后,大夫开始交待注意事项。并顺手递给她两块棉球。大夫的和气令她受用和感动,她向年轻的大夫投去信任的目光,并顺从地闭上了眼。
被人侍候的感觉,有时,真好。
强者以强者的面孔示人,强者容易被忽视。
江澜道不出人生悲苦,她坚信,有些路要自己走,谁也帮不了。
二十分钟后,江澜“到站”,但已筋疲力尽。
医院朦胧的灯光下,章新宇掏出钱夹翻看着江澜的照片。那时的江澜虽算不上校花,却也有无冕之王的称号。一米六八的个头,不高不矮,胖瘦适中。虽算不得美人,但五官大大方方不缺彩,俗话说好看不如顺眼,她骨子里透出一种不娇媚不流俗的气质,再加上她的乐观开朗、勤奋好学,为其大大提升了魅力指数。
江澜下了那张她期望值很高的大床,感觉有些头晕。她想知道此刻章新宇在哪里?她脑子里还充斥着关于报警的问题。她想马上见到他,刚一迈门槛就摔倒在地。别怕,一切有我呢。她瞬间想起章新宇的话。可是,可是他人呢?那个曾为她冲锋陷阵的大男孩呢?
多年的往事浮现眼前,大二开学返校,她在月台上排队等候。当火车缓缓停下,车门未开,人们就手提肩扛着大包小裹蜂拥至门口。江澜清楚,凭着一张无座票,还有自己单薄的小身板,差不多每次是一站到底。
三十多个小时,是站是坐靠的是运气。她踮着脚尖、抻长脖子、眼巴巴地从车窗向里张望。好像有个空座位。她使劲地敲那扇窗,一个女孩子心领神会之后,将头扭向一旁。江澜继续敲,女孩浮皮潦草地为她打开了一条窗缝,“帮忙占个座,谢了!”江澜大大咧咧地央求女孩:“窗户开大点,塞箱子进去。”对于她的得寸进尺,女孩不再理会。
最后,一个秀气的大男孩帮了她,把自己的行李包裹扔到座位上为她抢占了先机。那时的章新宇像个大姑娘似的。这是江澜为其下的定义。当然,章新宇并不认同。江澜一边说着谢谢一边往行李架上扛行李。江澜只是摆了个架势,替身很快就现身说法了——所有受累的事儿,章新宇全包圆了。
屁股没坐热,列车也还没启动,热气腾腾地挤过两个人来,在江澜身边站定,吵吵嚷嚷,比比划划,“这个座!就是这个座!”江澜觉得有人在拽她的衣袖:“来来来,起来,这座,她的!”江澜甩甩胳膊扭身向斜上方看,对方开口了:“还没听懂?这个座儿,她的,起来,赶紧地!”江澜有点懵,但她练好了坐功一动没动。
紧急关头,章新宇挺身而出,他挥手大概那么一指:“什么时候成你的座了?从上了车,我们就坐这儿。”章新宇强调“我们”的意思差不多就是:打群架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奉陪。
男子拉着黄毛女一边走一边安慰道:“嗐,八成记错车厢了。没事儿,跟我走,有你地儿!”然后又自顾自地抱怨:“这二十块钱挣的,容易吗我?”
江澜与章新宇最初的交往平淡无奇。他们本不在一个学校,一个在工学院,一个在财经学院。没有特殊约定,两人从不见面。直到大四那年,一次社会实践活动,大一的小师妹、省城一家公司洽谈会上的礼仪小姐,突然崴了脚,时间紧迫无人替代,章新宇请江澜救场。而江澜面临毕业无暇顾及那些看似风光的事。章新宇好话说了三千六,江澜勉强答应了。结果是,江澜一出场,风采卓然。从此二人开始交往,但并无深交。之后的一段日子,彼此失去音信。
毕业几年后,两人在一个特殊的场合相遇。一个突发事件成就了彼此。
“家属,家属帮一下忙!”听到声音,章新宇抱着江澜的衣服和皮包快步上前,这时,江澜的手机铃声响起。正是这个电话,让章新宇一夜未眠。
长久以来,两人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不翻对方笔记本,不互接对方电话,不打听对方隐私。他们认为这是彼此尊重最起码的规则。两人的感情在这样的行为规范中看似少了些热情和趣味,但也少了很多人都摆脱不掉的烦恼。掌控好尺度,各自为对方留有空间,对于两人感情的维系显得尤为重要。
“江澜,我是钟一梅,你钟阿姨,希望你能考虑一下我对你说的话!你等一
下……”对方稍做停顿:“小末,唉,这孩子,怎么又跑了,快回来,快点!江澜,
是江澜,你要不要听她说话?钟一梅在电话那头情绪激动。
章新宇拿着江澜手机从头至尾没有吐出一个字,他将手机紧紧地贴在耳旁,这时又有声音传出:“江澜,对不起,希望你能理解当妈的一颗心。小末病得很重,希望你能来看看他,我谢谢你!”
他满怀期望地欲听下文,对方得不到响应却挂断了电话。
已是更深人静,章新宇毫无睡意。江澜确实有事瞒着自己。他对此确信无疑。几次下决心想问个明白,但看到对方虚弱的样子,又感心有不忍。
吃过药,江澜的症状有所缓解。从诊断结果来看,没有大碍,也就是颈椎压迫神经,二三四五六七皆出现状况,常见病,医生也无奈。再者,多种头疼病,江澜到底属哪一种,仪器检测不出,依症状描述,又无法定论。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章新宇希望她能在家休养几日。可对江澜来说心病更难治愈。钟一梅是她的心病,确切地说现在她一想起钟小末便是愁肠百结,不堪言状。
钟小末当年在钟一梅的压力下,选择了背叛,而今又要重翻旧日账本,令江澜心生厌恶。这事儿倒也好办,不去理会便罢。可钟小末毕竟有了精神障碍。自己出现能有多大份量,他会有什么样的转机?他的病会痊愈吗? 一系列的问号在江澜脑子里盘旋。
俗话说,怕啥来啥。正当她左右为难、举棋不定时,钟一梅的声音又来了。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已是她第七次催促江澜,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次。
江澜决定去见钟小末,实属无奈。
作者简介:李红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长篇小说《单行道》获2016年《今古传奇》长篇小说一等奖,长篇小说《北归》获第二届全国昭明文学奖,长篇小说《秋水无痕》(合作)获德州市第二届长河文艺奖。

作品简介:青春无价,命运无常。故事由爱开始,因爱结束。
主人公江澜,拥有显赫地位和耀眼光环。一场事故导致她与出生不久即宣告死亡的双胞胎儿女有了再度聚首的机缘。由此,人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章新宇,在事业上与江澜妇唱夫随,相伴相依。多年来他从未停止为父亲的离奇死亡寻求真相。当谜底即将揭开,饮鸩止渴的他却遭遇不测。
书中主人公命运多舛,一次次面临艰难的命运抉择。江澜身患绝症,儿子遭遇绑架,女儿皈依佛门——以上种种的始作俑者是另一个女人钟一梅。
这是一曲悲壮的爱的挽歌。这是一段充满人性光辉的生命旅程。
当丑恶和风险同在,亲情与爱情共存,主人公如何实现自我救。
壹点号难忘秋月